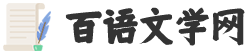据说有志于学术的女青年见到上面这两位,都有一种恨不能早生几十年的感慨。为什么?因为不仅学问做得好,更关键的:帅!
不少理想国的读者可能都认识,左边这位是史景迁,右边的是卜正民。
标题和开头这段话都是主页菌胡诌的,但也不全然无根据。
先说学问,史景迁是蜚声国际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北美汉学三杰之一;卜正民比史景迁小一辈,但其中国史研究先后获得汉学界极具分量的“列文森奖”和“马克·林顿历史奖”。两位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汉学界一等一的讲故事的高手。
再说颜值,早有颜值控称史景迁是汉学界的肖恩·康纳利,也确有好事者给汉学家们的颜值排过名,史景迁排第一,卜正民也不差,第二。
八卦到此,今天分享的文章,是作家杨照对两位的分析,相当专业,但值得花时间读读。研究历史的朋友,你会看到两种相反而有趣的研究方法;而对于一般历史阅读者,也许也可以激发你的思考:历史到底是什么?我们读过的历史书,为什么会这样书写?
顺做广告:理想国已出史景迁作品11种,仍有几种正待出版;卜正民的代表作《纵乐的困惑》去年由理想国再版,《维米尔的帽子》新版也于本月上市。
两种写作历史的手法
——谈史景迁《前朝梦忆》和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
文 | 杨照
1.
小大之辨
从我在台大历史系念书到现在的这三十年间,史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看待历史的方式,尤其历史学家看待历史的方式有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挑出两个和今天这两本书有关的面向,第一个我称之为“小大之辨”。
让我们先回到最基础的问题:历史是一件过于庞大的事物。因此,历史书写的起点是“选择”。传统史学面对同一个问题,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答案──历史要写“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不要写,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这个标准。换句话说,历史要写“大事”。正如小时候老师教我们写日记,老师都会说:刷牙洗脸不要写,走路到学校不要写,因为这是“小事”,是每天都会重复的事情。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有个根深柢固的传统──“看大不看小”。一个历史学家专注于细节,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并且是不对的。凭着有限的经历,面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的茫茫大海,我们只能去舀取最重要、最大的事件。历史学家如果不能辨别什么是大的、重要的,在过去的概念里,他不可以做历史学家。顶多只能做些掌故、笔记。
掌故、笔记有它自己的一套传统,它们由一些琐碎事物组成,它有一些独特的趣味,因此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传统。掌故、笔记虽有趣,但很抱歉,它不是历史。以过去传统史学的眼光检视,正因为有所谓大小之辨,所以会认为:人生当然也有无聊的时候,偶尔去搞一些掌故没关系,但是一旦面对人生的重要事件,如果你有兴趣要做一个史学家,如果你要当黄宗羲、要当王夫之、要当顾炎武,你就不能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掌故上面。那些是文人用零碎时间去做的事。
中国传统里面的这种想法,在西洋传统史学里面也有,而且一样难以打破。我念书时,在“史学方法论”这堂课里见识到各种不同的历史,眼界大开,发现到原来我们从小到大所学习的历史只是其中一种,就是政治史,原来在政治史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历史,例如经济史,人怎么吃、怎么活着,都可以用经济力量的变化和阶级互动来做最根本的解释,这就可以谈到马克思跟唯物史学的影响。还有社会史,人不是只有帝王将相,人类的社会可以分类成各种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决定世界的样态。
然而,二、三十年前,就算是我在史学方法论里见识了这么多样的历史方法,这些都还是“大历史”。为什么要讲社会史?因为社会上面有大事。社会上的巨大变革是政治史没有办法涵盖的,所以要讲社会史。但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兴起一股潮流,小大之辨不断被质疑、攻击。曾经我们认为,历史学家必然要关注“大事”,有这么理所当然吗?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呈现历史?再来,用过去的方法呈现出来的历史,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前朝梦忆》写张岱,跟卜正民(Timothy Brook)写维梅尔,这两本书都是近三十年来新的史学意识下的产物。在这一件事情上,两人属于同一股潮流,置身于同一个思想观念。到底这新潮流是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历史态度呢?它当然没有否定“大”的重要性,影响很多人的事情当然重要,可是要去呈现那些影响力巨大的事,不见得只能靠描述大事。
在这三十年当中,这场小大之辨相当复杂,如果你去看《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 Theory)的话就会发现,讲到历史理论时──更早以前可能说历史哲学──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会被谈到的历史理论只剩下一种,就是历史方法论。我们到底该怎样看待历史、怎样整理历史、怎样呈现历史?这三十年来的新潮流,。落实到史学研究与书写上面,倒不是说大家来写小的题材,而是我们应该“重视细节”。
史景迁
2.
从知识到体验
什么叫做“细节”?在过去的小大之辨里,如果要发现大的、核心的事物,必须先忽视、抛弃的一些其它不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细节。然而在这三十年当中,为什么“细节”一再被拿出来重新检讨?重新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历史渐渐从一个“形式上的知识”,移向“非形式上的体验”。
以前我们感觉历史是一套知识。知识是外于我的生命,是一些我可以整理、打包、带走的事物。但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它还要变成一种体验。意思是说,它不光是要让你知道以前发生什么事,它还要让你去体验、感受、经历过去发生的一切。这是历史学根本性的调整,它的功能与它的社会角色都起了巨大的变化。
很可惜我们的感受并不深切,也许大家做的事情并不够多。关于这种让大家不只是理解知识,而是体验历史时光的的精神,我们学院做的事很少,跟外界的沟通交流也很少。但是我们的确不能否认这是整个世界──尤其西方欧美史学──的重要主流。
知识跟体验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细节。当我们说“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这是一个知识的陈述,它可以很简单。但是,如果我想要把这句话变成一种体验,我就必须设法让你感受,这句话对活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的人,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冲击。我们必须换一种表达方式。
首先,当然要有很多的细节,它可以一层一层、不断往下降。第一个我们要先想想看什么叫做“统一中国”。背后是另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被统一了?我们可以用知识性的方式来简单回答:原来的战国七雄被消灭,剩下一个国家。
但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分析──透过细节。活在公元前二二一年之前与之后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生命经验?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细节:公元二二一年之后,所有出土的考古遗迹,道路遗迹上开始有了车辙。汉朝之后的道路遗迹,即使是石板路,都会看到一条直直的车痕,这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车同轨”所留下来的,这是在之前不会发生的事。
在这之前,不同的车有不同的轨距,所以路很难走。统一中国之后,后来的汉朝开石道时,便预先刻出同样的轨距以方便行走,这时候你就有了一种历史的感受,这就是统一中国。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汉朝人在官道上搭乘马车或牛车,它的概念比较像是“搭火车”,因为车子事实上是走在凹陷的轨道上的。这叫做历史体验。如何从历史知识中提炼出体验的感觉,是需要细节。如果没有生活上的细节,我们不可能从知识的理解变成体验的想象。
在这一方面,史景迁和卜正民都是可以带给人精采体验的作者。例如史景迁写张岱、以及过去他所有写过的人物,他的写法如一,必然会累积众多细节。《前朝梦忆》一开始就写张岱的回忆──当然,张岱是很好的题材,因为他留下了太多的材料。
史景迁会一路告诉你他怎么跟叔叔讨论泡茶的学问,要用怎么样的水可以泡出最好的茶?接着他回忆起他的祖父……史景迁将许多材料聚拢,他强调眼睛所能见到的细节。例如张岱回忆他的几代先人时谈到了科举。如果写一般的传记,用大事纪式的写法,这类主题必然放在最前面,劈头讲他的第四世高祖哪一年中举,他的祖父哪一年中举,一口气写完了,整个对他的家世做一个交代。但史景迁的选择当然不一样,他会告诉你考场里面的经验,一个考生怎么样进入考棚,在考棚里面会发生什么事……他要你去体验、去了解什么是“晚明文人的生活”。
那么卜正民呢?他对于细节的察觉更直接、更清楚。这一点从《维梅尔的帽子》的封面就可看出,卜正民用阅读画作而写成一本书。不仅如此,他还花了很大的力气在阅读画中的帽子。就是这么一顶帽子。这幅画画的是跟一名女子在对话,卜正民捕捉这顶帽子每一个可能的细节,从这个帽子到这幅画,延伸到与维梅尔相关的任何一个细节,他通通不放过。
所以,在写作方法、或历史的研究方法上面,他们两个人是一致的。我们都可以叫他们“细节史学家”,他们不放过任何的细节,他们追求的历史著作正是由细节构成,这是他们最习惯、也是最喜欢的写作方式。从最一开始我们说的,今天为止历史学上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在这两本书里看到。
卜正民
3.
向文学取径:历史叙述的策略
另外一个近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史学界愈来愈重视narrative,叙述。“叙述”以前被视为理所当然,始终都是方法的一部份。是的,作为一个史学家,依照以前的标准,你当然要“能写”,你要有基本的文字功力,史书基本上是用文字写的。史学方法基本上可以直接用一个章节告诉你怎么写历史论文,它有什么规范、规矩、规则。这不是我要讲的narrative。
以前历史学界认为历史有一种标准答案式的写法,那是刻板印象,在这二、三十年当中,史学界开始向文学取径,从文学中获得巨大的刺激、灵感、借镜、参考,开始意识到各式各样的叙述策略。同样的内容与材料,可以说不一样的话。所以“叙述”(narrative)与“叙述学”(narratology)是近三十年来史学第二个重大改变。
史学界从文学那里发现,没有必然的叙述。以前我们会说,最好的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如果学会了史记那套叙述模式,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史家。在西方,你去看普鲁塔克(Plutarch)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历史应该要如此生动。
但是,现在我们不把史学当成技术了,史学方法也不是问题的答案,反而是一道“问题”。新的问题就发生在新兴史学家心里面,不断逼迫他们去思索──我所面对的读者是谁?这就是叙述策略!
以前的史学家从不想这些。但现在,史学家怎么可以不去想想读者是谁呢?不一样的读者对不一样的事情有不同的感应。所以史学家要有一些本事,这套本书叫“叙述策略”。掌握了历史的数据,在组织、整合、呈现的同时,要不断地反问:“要给谁看?”进一步再问:“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最有效地呈现我想要呈现的内容?”如何打动想象中的读者,让他们读到我希望他们读到的东西?
从叙述策略的角度来看,卜正民与史景迁恰恰相反。他们同样爱好细节,但两人手法各异。
4.
让陌生变熟悉
容我这样说:史景迁的叙述策略比较接近“让陌生的东西变熟悉”。这牵涉到他的写作背景与环境,史景迁刚从耶鲁退休,之前长年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史。如果你去翻查史景迁的资料,你会发现他很少在期刊上发表史学论文,他写的几乎都是给美国一般社会大众的书。他在耶鲁开的课也一样,他的对象多半不是针对研究生,都是大学部的课。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面对的是一群美国第一流、最聪明、也最讨人厌,最自以为是的年轻学生。他们进入长春藤名校,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史景迁教学时,面对的是这群年轻学生,而他写书时,面对的是美国一般大众。这两群人有个共通点:他们不那么了解中国史是什么,而且并不清楚自已认知上的模糊。
我在哈佛当助教时,一旦学生发现我这个东方人,会立刻抓住我,和我谈老子,他当然觉得他懂,然后他要比较老子和尼采,看你懂不懂尼采。他们吸收了许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然后渐渐形成一股傲慢。美国社会大众也一样,大部分的人对中国有一种“大概是什么”的想象。因此,当史景迁透过一层又一层的细节,编织其著作时,面对的是这股傲慢。他要让这些美国人了解到,他们其实对中国历史陌生无比。
我们如果看史景迁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对我们这些学中国史的人来说,老实讲,这本书并不值得读,它描述了我们“早就知道”的那些人,把跟五四运动有关的人物传记拼凑在一起,替他们做了一部群传。像鲁迅这样的名人,史景迁在《天安门》写到任何一件事,大概没有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的。
但这本书毕竟不是为我们这种人写的,它的叙述策略不在我们,他的重要性也不在我们。史景迁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清楚认知他的读者,他知道他的读者不懂May Fourth,他们只知道一个笼统的“中国革命”。美国另一位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大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对美国人来说正是这样,中国有个大革命,就像法国有个大革命,俄国有个大革命一样。但革命的细节,例如五四运动,他们全然陌生。
你如何让一个人对他完全陌生的事情感到有兴趣?如何让他觉得,一件遥远、陌生的事情,是他值得知道的,并且进一步让他一点一滴地体验?史景迁必须累积、堆栈这么多的细节,让你感觉到历史里的每一道纹路与肌理,都在你可以抚摸的范围之内。透过这种策略,他让读者亲近了中国历史,亲近他笔下所写的人。
他用同样的写法写张岱,聚拢所有搜集得来的材料,巨细靡遗,几乎没有任何遗漏。他并不打算提供新鲜的观点,或者让你知道其它研究张岱的人不知道的事情,作出一些其它研究者会吓一跳的结论,而是将所有材料组合成一个丰富且易读,引人入胜的人物完整写照。所以他擅长组织,习于编织。
史景迁往往从一些特殊之处着笔,让读者感到吃惊。他会告诉读者说:欸!以前有人在很遥远的地方用这种方式过活哦。你以为接下来会有一个传奇故事,就像魔戒或飞在天上的龙,不是。接下来,他铺陈所有的细节,告诉你,事物有其道理,并且你可以体会、可以理解。
我认为这是史景迁最重要的写作方法,他成功地把所有陌生的东西化为熟悉。所以我们读史景迁的书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了:如果他要写的对象是你本来就熟悉的,你不必读,因为你不会在里面读到特别的观点、特别的解释。但如果他写的题材是你本来就觉得陌生的,没有比史景迁更体恤你的作者。像对很多人来讲,张岱是陌生的。那么,读他就是一件愉悦的事。
5.
你真的知道吗?
卜正民也很重视细节,但他的叙述策略刚刚好和史景迁相反──让熟悉变陌生。史景迁会告诉你,你觉得这顶帽子很奇怪吗?不,这帽子一点也不奇怪。而卜正民会问你:你觉得这帽子再平常不过吗?对不起哦,我告诉你,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他们不同的策略。
《维梅尔的帽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卜正民面对的西方读者眼中,〈与面带笑容的女子〉这张画是他们的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没有人会觉得这张画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会连接不断,丢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你知道他的帽子吗?她为什么要包头巾?窗子为什么要这样开?画面的后面有什么?地图为什么要挂在这里?
我们再看《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少妇》这幅画。对于看过这幅画的人来说,没什么神秘之处。但卜正民会问:她在读什么样的信?他会透过他累积的材料来说明,她应该是在读一封来自远方的信。而这个“远方”是荷属东印度公司。
再来,她的身边有一张床,床上有一些水果──我顶多读到这里──但卜正民会进一步问说:水果放在青花瓷盘上,这个盘子为什么会在荷兰?
接下来,还有我们真的不会看到的东西,卜正民看到了。这个读信的女子后面,有一堵空白的墙。研究艺术史的人透过X光,发现维梅尔本来在墙上画了一幅画,后来却涂掉了。卜正民会告诉你,维梅尔他为什么要画那幅画,后来又为什么要涂掉?
这就是卜正民。他会逼问你:你真的看到了吗?你真的知道吗?本来理所当然的事被他愈搞愈复杂,本来我们自认为熟悉的东西,但他弄得愈来愈陌生。他选择这个策略自然也有原因。因为他要面对的读者,与他所想要产生的效果,和史景迁是不同的。
他面对的是那些已经有所了解的人,例如,我们可以在书上读到安东尼‧贝利(AnthonyBailey)的推荐:“有些人自认已把十七世纪的尼德兰摸得一清二楚,但他们若是读了卜正民这部精彩之作,肯定要大为震惊。”
是的,自认为一清二楚的人,将接到卜正民的挑战。正如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已经对这题材熟悉,史景迁的书不打算对你多说什么。但你以为你对十七世纪的尼德兰再熟不过?卜正民正是要向你挑衅。
所以,读这两本书有很多不同的效果。如果你读完了史景迁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我敢肯定会一连有好几天,张岱会时时出没在你的身边。曾经那么陌生、十六、七世纪的一个明朝人成了和你长相左右的人。
但读卜正民的书刚好相反,把《维梅尔的帽子》从头到尾读完。我想,你大概还是不知道维梅尔是谁,你不会对他有什么清楚的感受,卜正民要做的事不是这个。他只是想告诉你:第一,从十六、七世纪开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彼此连结、彼此互动(interconnect);第二,凡事都是有个来历。
他另一个叙述策略是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这些事怎么来的?我们享受了这些事事来历的答案。一旦我们反过来追索它们的来源,所有的事,我们曾经以为简单、必然的,顿时成了一则则丰富、生动的故事。
他从维梅尔的帽子讲起,一开始先谈论这种帽子和荷兰军事的关系。这种帽子不是在欧洲生产的,而是在加拿大。因此这个帽子的材料,必须从欧洲人到加拿大的殖民谈起,而欧洲人到了加拿大,碰到当地印地安人,之间又擦出什么火花?一个一个问题丢出去,一顶帽子拉出一个世界。
6.
最好的时代
从写作方法论上面看,史景迁和卜正民都是细节史学家;从叙述策略看,他们恰好相反,一个要把陌生变熟悉,一个要把熟悉变陌生。这大概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最后,另一个最重要的共通点,为什么我们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谈?因为这两本书谈的都是明代。
一九九九年,纽约《时代杂志》做了很大的专辑。千禧年即将来临之前,他们回顾了过去的一千年。访问了许多的史学家,问他们说:“如果你不是活在今天的世界,那么你最想活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我记得很清楚,史景迁回答:如果他生活的时空不是二十世纪,他希望自己能活在十六世纪的中国。
十六世纪的中国就是明朝的后半叶,那的确是一个极其辉煌的社会。他们没有问到卜正民,但我想他的答案也差不多。看他写的《纵乐的困惑──明朝的商业与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联经出版),他挖掘出的明朝人的纵欲和享乐,直到今天都还令人惊讶。
但我想十七世纪吸引这两位史学家的理由,大概不只是这些纵乐。从十六世纪开始,中国从明朝进入到清朝,其中的变化种种,对任何一位史学家来说,都是令人振奋的挑战。一个完熟而散发出阵阵香气,正准备开始腐烂的文明,外来的事物陆陆续续进入这个文明之中,和它起了互动。在这之中,任何一种misunderstanding(误解)都曾经发生。
这个世界从未学过要如何彼此沟通。正因为这个世界从未学过,沟通是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极其热闹、极其灿烂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都在这个created misunderstanding中发生。对一个拥有高度历史敏感性的人来说,这里有太多太多历史的题材,没有比这更好的时代。
即使是今天的我们,着眼十六、十七世纪,大概也会有诸多感慨。例如,对研究台湾历史的人而言,大概也没有比这段更精彩的题材了。但许多漂亮的题材到今天都无法好好的整理。史景迁让美国人体验张岱。我在想,台湾有没有人能写郑芝龙呢?有没有人能写郑成功呢?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了解郑成功,事实上还有太多我们尚未厘清的事。
看看郑芝龙吧。他的出身是荷兰的通译,他的生意遍及整个东亚海域,北达日本平户,于是他娶了个平户女人,生下了郑成功。他的基地是今天的澎湖、金门,这个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中国人。这是一个陌生人。我虽然不曾研究这方面,但我想我们总有方法锁定一些问题,例如他为什么会去当通译?他怎么学会荷兰语?他和平户的关系是什么?在过去的东亚海域,郑芝龙如何和他的仇敌厮杀,如何和朋友往来?
郑成功的角色又如何悲剧?他的妈妈是平户的朱印船主之女,但郑芝龙为了拉拢明朝,把他送进国子监读书。这些人物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明朝过于丰富,有太多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这时候不就需要有一个像史景迁一样的人,把郑芝龙这样一个陌生人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体验吗?
同样的,在那样十七世纪的台湾,稀奇古怪的力量互相作用,卜正民曾经在《维梅尔的帽子》里谈及每一件事物:毛皮、茶叶、烟草……都可以和台湾有关。但谁能从这些文明变化的细节中牵扯出台湾的历史呢?
藉由阅读这两本书,我希望我们不只得到这些作者想给我们的,同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风格中得到一些启示。他们如何看待历史,这样的价值如果能在我们的文化里生根,在诸位的脑海中刺激出雄心壮志,那么我们的收获足矣。
文章根据2009年4月4日杨照在诚品敦南店“浮华与苍凉”系列讲座演讲内容,由林姿君、李静慧整理,有删节。
【相关图书】
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加] 卜正民 著 黄中宪 译
理想国,2017年8月
(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
《维米尔的帽子》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马克·林顿历史奖”获奖作品。作者通过七幅油画、一件荷兰产的青花瓷盘上的细微之处,探寻其背后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在看似无关的普通器物中,看到荷属东印度公司兴盛的跨洋贸易,看到的毡帽里隐藏有寻找中国之路的热情,看到一条由欧美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之河、烟叶数十年间便风靡世界各地。
17世纪的人们,依托航海技术的发展,跳脱出囚困自己的周遭,想象并追寻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们赌上故乡,奔赴各地,将世界连为一体。一些普通人也被贸易旋风吹起,撒落到异国他乡。世界曾经孤立的的地区被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网络,这个变革没有人预测得到,也无人能够扭转。四个世纪以后的我们,对此恍若相识。
商业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至:chenteng@imaginist.com.cn
转载:联系后台 | 购买图书: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