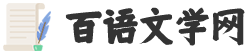我读本科时,很多课程都未逐丝习读。绝大多数时间都交付自学,在自习室,图书馆,湖边的草坪。然而每天阅读和写作的时间,往往超过八小时。周末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去自习,更是平常。现在想来,顺制模式和自役模式各有各的风景。同时拥怀公共经验和私人记忆的俏丽,不仅贪婪,而且愚蠢。
如今也做教师,对曾经并未那么尊敬的老师表示平等心的歉意。欢喜的是,对老师们的著作,也开始拥有更具内心性的体味。至于我曾经偏执的选择,它更多的是自我的放逐,高傲、愤怒与孤独的承载器皿。必要,也必须。
当时中文系的文学氛围已趋破碎淡漠,庸俗的“语文学”和木制的“文学学”,在那时已浮现丑陋的端倪。我那时以为,文学本身,并无理论。一位大谈文学理论的老师曾愤慨地说:,非黑即白!”那课遂再未去。当然我感谢前六排女生们的笔记,虽然她们极尽自然主义记录之能事,包揽后来所有的保研与外推名额。
2004年春,学科专业方向介绍大会。注意,大会性质。一位外国文学老师上台后,第一句话:“同学们,读我们中文系,也是有机会出国的!”我联想起曾经的中学语文老师所说:“卡夫卡,是巴西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这个错比前者,错得轻,错的没有异味。
在这几年的本、硕毕业答辩会上,我格外赞扬了几位专注于文学创作与人文研习的同学。当然,论文也明显的好。我一直以来有这样的心声,给予这类年轻人以应有的认同和足够的尊严。中文系的正命,因文学的拓荒而繁华。在文艺青年里,许多都是嗅着时尚和异性的气味在油滑漂移。傻站着,傻坐着,总吃亏的,多是文学青年。尽管硬性的孵化晶体,也注定隶属于他们。
现在的意见,源于过去的所见。一位大我一级的文学挚友,当年考研失利,毕业也不顺,后来狼藉离校。临别饭馆匆促小聚,他叹言:希望未来能创造一种理想机制,惟愿人能人尽其能。我不为他叹息,也不强求他建设强悍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失利者,是中文系曾经在胜利时节精神山峰上的战旗。愈辛酸晦暗,愈迎风招展。
那时觉得很多文学家的话,听得,信不得,又颇丧气。回溯这条隧道的往事体感与抒情细胞,我最青睐意大利传奇硬汉球星迪卡尼奥的经典自传《天才与恶棍》里那段无法抗拒的结尾,它似乎与一切迎风孤立的感言先天通电:
无论发生什么,我将继续过一种无悔的生活,我将继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后果如何。最重要的,我将不断回顾走过的路,记住我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