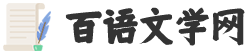作为哲学与当代艺术领域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关于技术与物件的讨论到底意义何在?技术与诗歌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如何看待“物”?
由画廊周北京联合单向空间、单读共同主办,一场以“当代艺术与哲学中的科技与物件”为题的对话在 UCCA 报告厅内举行,著名艺术家汪建伟、著名学者汪民安、青年诗人与学者戴潍娜就此展开了一场深入而广阔的讨论。
▲主持人陈楠,艺术家汪建伟,学者汪民安,诗人戴潍娜(从左至右)
我今天基本能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好的艺术就在于它有巨大的解读的空间,真正完全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第二个结论就是我们唯一的平等就是无知。
——戴潍娜
世界也好,作品也好,不要追求什么客观性,不要追求一个唯一性。作品在不同的历史当中,是敞开他的意义的,世界的活力或者作品的活力就在多元性和丰富性。
——汪民安
你必须用你自己的方法和态度去看这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有各种命名方法,不一定只有“时代”这一种方法。你可以问问不同的人,你认为你是处于什么时代,我相信一个进步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因为如果这么多人活在一个单词里,这个世界是不值得活的。
——汪建伟
消费社会实际上就是今天的物对人的挤压
主持人:为什么选择一个看上去如此抽象的话题?
汪建伟:我工作室每天碰到的就是这两个问题:技术和物件。而且我记得当时提议的话题挺大的,要让我谈这个时代,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时代”必须是你自己能够触摸到的,那个时代是跟你有关的,不是从媒体上听来的。
汪民安:最近十几年,不管在哲学还是艺术领域,物和技术是两个热点话题。技术就不用说了,现在不仅是哲学与艺术讨论技术,这已经是全社会的焦点,包括人工智能。至于为什么讨论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消费社会实际上就是今天的物对人的挤压。我们从 20 世纪早期就开始谈物化问题,关于物的问题一直是二十世纪文化的重要维度。
戴潍娜:我自己是写诗歌的,诗歌写作的技术跟诗歌写作所面对的物,我发现同样是适用的。这两个关健词如果放在诗歌领域内,它同样是一个值得反复去辩驳,并且能够得到很多雄辩性的结论的两个重要的关健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哲学、技术可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去探测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根本性的焦虑和发展方向,这就像一座山上不同角度的人们,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上山,但当他们到达山腰或者到达峰顶的时候,他们看到的风景往往是触碰在一起的。不管是哲学,物理,诗歌,还是数学,它们的制高点一定是触碰在一起的。最好的数学也是最好的诗歌,好的哲学本质也是好的艺术。
▲青年诗人、学者戴潍娜
每一个工具都把你从身体的局限里超越出来
主持人:维娜,你作为一个灵性诗人,如何看待现阶段快速发展的科技和技术对你的影响?
戴潍娜:很多人都想把科学跟人文做一个对立的二元论的论述,首先我们要破除这个二元论。维多利亚晚期的人,很多都是打破学科间壁垒的人,很多人精通技艺、哲学、医学,同时又是很好的文学家、艺术家。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由于学科的不断的分化,我们开始变成了专业化的人,变成了还没有来得及见到整个森林,就已经钻进了毛细血管里的人。
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而言,让一个诗人去讨论科技可能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回到赫胥黎的年代,你会发现他们的写作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艺术,他们的人文性思考从来都没有离开他们对科技的关切,很多甚至是由对于科技的关切而触动的一些人文上的启发。
主持人:汪建伟老师,在您的艺术创作中,科技的发展会带给您一些新的冲撞吗?
汪建伟:福柯的《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里,康德谈启蒙的时候有一个词特别吸引我,这个词叫出口,其实就是出走。他认为启蒙就是让你从一个不成熟的状态走出来,这个出走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绝对不是一次性的动作。这种出走要通过技术来实现。对于艺术家来讲,技术是画油画的笔、是做装置的刀、是做雕塑的工具。每一个工具都把你从身体的局限里超越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就是一种真正让你和这个世界保持不断启蒙的状态。
▲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
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有一群人,他们直接讨论物,重新让我们从围绕着物本身的媒体上撤退。就像有时候我们去看展览,有的人说懂了,有的人不懂,但实际上我们是通过知识、经验去触及到那个物,但那个物到底是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物,这是要提个问题的。
主持人:您不相信经验的重要性吗?
汪建伟:经验当然很重要,但是经验的作用也包括自我封闭。就像药一样:药能够治病,也能把你毒死。
▲艺术家汪建伟
主持人:汪民安老师,您怎么看待刚刚汪老师所讲的经验可能所带来的局限,以及怎样才能够跳过这些回到本原呢?
汪民安:思辨实在论是近十来年欧洲的一个年轻哲学家群体,他们组织了一个专门研究物的哲学小组,他们谈物的角度不一样。福柯和德里达等所谓的后现代哲学统治了哲学界大约五十年,不在他们的思想之下很难呼吸,即便可以呼吸,也永远达不到他们的高度。沿着他们的线索很难走出来,为了找到那个“出口”,思辨论这些人开始反对康德以来的这一套主体性哲学、关系主义哲学,重新强调物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一个绝对的客体,但不需要通过逻辑推理去了解它。所以他们开创了哲学的新时代,与两个时代的哲学都不一样。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 - 2004),法国哲学家、西方解构主义代表人物
艺术让我们不断地成为他者
主持人:我有一种冲击感,好象回到了学生时代,这么一个短暂的高密度对话,能够让人意识到自己认知和理解的局限,这是学科交叉带给我们的冲击感最有意义的地方。我不知道潍娜怎么感受,或者说在做诗歌当中受过这种冲击感吗?
戴潍娜:可能所有的艺术都是让我们不断地成为他者的一个过程。奥威尔年轻的时候受过一家左翼出版社的委托,去考察在此港的一个工人阶级的状况,当时奥威尔坐在非常豪华的列车包厢里,在路上他居然看到,车窗外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大冬天里走出来,蹲在那里掏水管,姑娘脸上有那种贫民窟特有的憔悴的颜色,她应该很年轻,可能才二十岁,但是看起来已经像一个三十岁的人了,她蹲在那里把手伸进水管里去掏已经堵塞的水管。这个时候,坐在豪华包厢里的奥威尔就成为了所谓的他者,他经历着双重的苦难,一方面他成为了贫民窟姑娘,感觉到她此刻的悲惨,另一方面他在豪华包厢里经历着作为一个作家良心上的焦虑跟折磨。
另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概念就是熵。这个时代可能是一个熵不断增加的时代,不断在变得更加混乱。这样一个混乱的所谓平凡天才的年代会走向什么方向,现在我觉得任何人都很难下定论,但是它确实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颠覆性的世界窗口。
主持人:汪老师,您怎么看待这种阶段性的混乱?
汪建伟:任何趋于这种混乱发生的时候,就有一种力量——负熵的生成。今天的理解方式,就是以毒攻毒。既然我们现在身处熵的时代,那任何逃避都是非常懦弱的表现。技术进步了以后,给了人提升更大的空间,把人从传统的、不可理解的东西带了出来。以前我们说人定胜天,人一定要控制工具,如果掌握不了工具,就不是一个很成功的艺术家,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想法。
今天这个“主体”、“客体”、“我”、“世界”、“社会”、“文化”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世界,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我们谈跨界,实际上不是在说跨界,因为每个界自己独立支持的世界不存在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世界重新看一看,努力去克服每一个界以前的知识教条,也许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个体才会出现。
▲学者汪民安
思想真正有启发的时候,会有强烈的快感
主持人:汪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被冲击的痛苦?有些东西可能你已经固有地认为它是这样,当一些新的刺激、冲突袭来的时候,你要强迫自己打破原来的认知。
汪民安:如果学习到的东西都在你的知识范围、理解范围之内,都是你的熟悉方式,读书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一本书如果打开了一个世界,我读到这样的书的时候,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类似于关在一个屋子里忽然把窗户推开。我觉得思想上真正的觉得有启发的时候,或者让你打开一扇门的时候,会有强烈的快感。
戴潍娜:快乐跟痛苦是两样非常相近的物质,并且它们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相互转化。我们去回想自己最大那些快乐往往都是经历了一些痛苦之后变来的,而有的时候,此刻经历的快乐会转化为日后最大的痛苦,所以快乐跟痛苦之间的临界点是非常微妙的。
▲活动现场
艺术家不是发现真理的那个人
汪建伟:我们被常识所控制,战胜陈词滥调要从流行词开始。比如说当我们说“痛苦”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用去想这个词后面什么意义。回到一开始说的“去关联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去美术馆看展览,你第一次面对这张画、这个雕塑的时候,可能会说看不懂,旁边也许就有人告诉你,这个人是女性艺术家,在哪受过教育,受什么影响,讲了半个小时,你说通过你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但其实这个物在他介绍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变化,是解释让你理解了这个物。但是这个物是不是他讲的那个东西?可以想象。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思辨哲学里面有一种理论,认为原本的那个物永远是空缺的,是在到来的过程,不是在等待你。这跟拉图尔说的很像,他认为真理不是“发现”的,是被“建构”出来的。机器、工作人员每天通过数据、图表,然后再把很多存在的科学杂志拿来对比,有了一个自己的程序,变成一篇论文,论文在科学杂志发表,引起争议,争议就会被人引用,引用多了就变成事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科学真实。
科学家的神话跟艺术家一样,艺术家并没有在屋子里,最后终于把真理找出来了,艺术家不是发现真理的那个人,不存在一个事实、真理是被发现的,关联主义却让你有这种幻觉。
主持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受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独立地去掉这些关联性,去理解作品本身呢?
汪建伟:任何一个人面对不熟悉事情的时候,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知识之间的不对称是社会每一个人的分工与身份造成的,不存在高、低和由于谁占有知识量的不同我们就认为懂不懂。我觉得我们都是普通人,任何人都有自己无知的一面要面对。如果一个儿童问我关于玩具的玩法,我会觉得自己业余,但这个儿童也会说,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艺术问题。这是平等的,这个时候不存在知识的高低,也不存在谁对谁有一种知识权利,在不懂的程度上,人人是平等的。
▲现场读者
单读出品,转载请至后台询问
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至朋友圈
▼▼点击【阅读原文】,打开《偏见》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