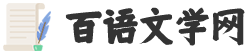周勇. 难逃厄运: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学兴衰史[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2): 102-110.
摘要:由于急于确立学科地位与影响,更因为没有充分估计当时教育界的主流学术及文化范式,1919年兴起的教育学固然通过大规模推广“道尔顿制”得以在教育界迅速产生巨大影响,但却只能让学术界将教育学等同于缺乏学术、文化内涵的“教学法”研究。教育学因此难逃学院生存厄运。回顾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学兴衰史,可以为反思当代教育学的理论生产方式与学术文化品质提供有益参照与教训。
关键词: 20世纪20年代;教育学;新教育运动;道尔顿制实验;学术文化
作者简介:周勇(1973— ),男,江西南昌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
TheUnexpected Misfortune: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in China in the 1920s
Zhou Yo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To obtain academic position andacknowledgement in the shortest time possible,the pedagogy,which rose in 1919,exerted immediate tremendous influenceon the basic education reform by implementing the borrowed “Dalton Plan”through the country. But this academic effort could only make the dominantacademic circle regard pedagogy as the studies of “teaching arts” which had nosound knowledge or cultural underpinning. It was this low academic evaluationthat caused the unexpected misfortu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in the1920s,whichcan provide a historical insight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academic quality ofcontemporary pedagogy in China.
Key words:the 1920s;pedagogy;The Chinese New Education Movement;the Dalton Plan;academic culture
一、教育学的兴起及其学科内涵
事情得从1914-1920年间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刘廷芳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陆续回国进入教育界寻求发展,以及“五四”时期杜威访华传播其教育学讲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生回国后总体做了哪些事情,丁钢[1]、周洪宇[2]等近些年已有初步考察。这里仅从“教育学”角度强调,正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生归国及杜威访华这两股力量促成了“五四”以来教育学的兴起,并因地域不同,从1920年起还产生了南北竞争颇为激烈的教育学格局。
南派以南京高师为基地,健将有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等,关系网络包括北京大学、江苏教育会、浙江教育会、商务印书馆等。北派以北京高师为中心,主力包括刘廷芳、邓萃英等,可切实仰仗者则为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北高师曾试过联络蒋梦麟及北京大学,但因后者只想让北高师把其1920年规划的“教育研究科”并入北大,未能达成合作。北高师认为,蒋梦麟及北大是为了在即将兴起的教育学界占据“龙头地位”。可以说,自一开始,北高师一方便处于弱势位置,其教育学生产计划也因不利体制处境在最初几年里总是难以开展。
在借助杜威访华的影响力这一点上,北高师的表现亦不如南高师一系。当初促成杜威访华的是陶行知、郭秉文和胡适等人。[3]4-5杜威在中国讲学、演讲的两年期间,组织安排之权亦是掌握在南高师一系弟子手里。这当中胡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杜威来华之前,胡适便已爆得大名,陈宝泉、刘廷芳等根本无法望其项背。杜威来华之后,活动能力极强的胡适更是主动引领杜威的地域与言论走向,使杜威之行可以进一步巩固、提高其声望与影响力。直到杜威1921年7月离华,北高师一系弟子也未能将杜威所到各处的风光占为己用。
紧接着,另一位重要人物孟罗(今译孟禄)来华。如胡适日记所示,北高师同样试图“极力垄断孟罗,想借他大出峰头”。但孟禄却“怕北大一方面因此同他隔绝”,竟主动请郭秉文帮他联络正如日中天的胡适。刚刚送走杜威的胡适“因为看孟罗的面上,不能不去招待”。[4]478然后孟禄又请胡适引他去见蔡元培。对此各路学人相互争夺西方人物,今天有学者曾将其概括为“挟洋自重”,[5]可谓切中要处。鲁迅作为当时的旁观者,看得更明白,如他所言:“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6]109只不过,今昔论者在分析本土学人“挟洋自重”时,似乎都忽视了其实杜威、孟禄等西方人物也能摸清,谁是势力或影响更大的掌权一方,否则也不会听其安排,乃至主动靠拢。
一言以蔽之,“五四”以来教育界兴起的教育学将有何种实际表现与成绩,主要取决于跟胡适、北大关系甚密的南派教育学者。当然,北高师1920年以来的教育学机制建设亦应当为日后结果承担责任。,[7]便注定无法让教育学在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彼时各路学林高手那里留下良好学术印象。但谁又能预料日后发生的事情呢?刚开始时,似乎也只能先把阵容凑起来再说了。
况且即使阵势凑起来了,也不如南派一系壮观,还是只能看着南派同行自“五四”起,以一轮又一轮的行动来彰显教育学的学术生产能力。众所周知,这一轮又一轮的行动总称为“新教育运动”。从1919年2月《新教育》杂志创办开始,到1925年10月《新教育》停刊,这一运动持续了6年8个月,堪称教育学兴起以来规模与影响均为最大的一次亮相。杂志最初由“新教育共进社”负责编撰,成员包括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底,北京高师方才加入。至于作者阵容,则十分复杂,有蒋梦麟、郭秉文、汪懋祖等各级教育行政领袖,又有汪精卫、,还有胡适这样的学界权威,此外便是陈鹤琴、刘廷芳等相对专业的教育学者。
作者队伍中本就缺乏一流学者,且背景如此复杂,想法不一,显然不利于教育学形成统一有质量的学术形象。就《新教育》到底生产出了什么样的教育学而言,最拿得出手的教育学作品似乎就是“杜威号”“学制研究号”“孟禄号”等十个专号,其中胡适最看重的是“杜威号”。[8]加上杜威两年各处演讲,杜威教育学确乎就是“新教育运动”所贡献的最成样子也最有影响的教育学。那它将“五四”以来的主流教育学生产塑造成了什么样子呢?大体就是拿着杜威一系的美国教育理论,到各地中小学发起教育教学改革试验,借此掀起所谓杜威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教育学运动。
连远离《新教育》杂志的乡村小学教师钱穆都曾试验“五四”时期突然崛起的杜威教育学。如《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所叙,为了验证杜威教育理论在小学是可行的,钱穆竟停下此前的先秦诸子研究与教学,花三年时间一定把杜威教育学试验做成给同事看。[9]119当然,钱穆毕竟远离“新教育运动”中心地带,其教育学试验再成功,都不可能成为五四以来的典范教育学实践。
舒新城才是当时教育学实践(试验)最有影响的典范,或者说,“五四”以来兴起的教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文化实践,在舒新城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教育史学界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舒新城登场,“将‘新教育’改革运动推向了发展的最高潮”。[10]93其教育学生产成绩与影响是否也能大过南北高师两路教育学者,这里不好判断。不过,其教育学讲演、授课在“江浙皖鄂湘各省”中小学的确影响很大,乃至实际只有本土高师毕业文凭的他常被误认为是“哥伦比亚教育学院教育博士”。等“新教育运动”结束了,他仍被成都教育界当作“东南大学教育学士”请来演讲。[11]82-83
可见至少在基础教育界,舒新城已被视为一流教育专家。那他贡献了什么样的教育学呢?和钱穆一样,舒新城也未超过蒋梦麟、胡适等杜威器重弟子勾勒的教育学框架,亦是在中小学教育界实验杜威一系的教育理论。只不过,钱穆从杜威那捕捉到的是“课程生活化”;舒新城捕捉到的则是“道尔顿制”,然后便在中小学实验、推广“道尔顿制”。这一教育学实验开始于1921年,最初试验基地包括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和东南大学附中这两大示范学校。这一实验堪称教育学在教育界迅速崛起,产生影响力的重要机制。光1922年底在《教育杂志》上做的一期“道尔顿制研究专号”,便让“全国轰动,各省教育界之来吴淞参观者络绎于途”。[12]225半年后,全国实验“道尔顿制”的学校多达数百所。[13]223
期间(1923年12月),胡适曾到东南大学演讲古代书院,也不忘先肯定“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14]273仿佛要为“道尔顿制”实验注入更多本土底气。胡适演讲那年,舒新城也在东南大学开设“道尔顿制暑期学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十二个省份”。“学习班结束后,舒新城又到上海、武进、宜兴、武昌、长沙各处演讲”。短短三年之内,教育界便生产了“道尔顿制论文共150篇,其中舒新城一人发表“21篇之多”。影响的确大,大到出乎意料。舒新城本人也注意到,连“那些借教育为啖饭之地的官僚政客、军阀流氓”,也“纷纷借行道尔顿制为升官的筹码”。[15]
为实验、推广“道尔顿制”这一美国教学制度,而在各地中小学奔波忙碌的舒新城似乎不知,胡适一系教育界的学术权威正在生产何种学术文化,以及“道尔顿制”在各地炒热之后的种种迹象,又会让教育界各路学术权威如何看待教育学的学术形象。由此想起,叶澜在分析“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世纪问题”时,曾提醒教育学同仁注意,“人们更愿意把教育学界与中小学教师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学术界联系在一起”。[16]很明显,“人们”之所以容易觉得,教育学是“中小学教师”做的事,或者“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把教育学看作“学术界”的一种学术文化,其实也是因为教育学自身学术定位所造成:自一开始,教育学便只顾尽快深入中小学,热衷于向中小学推广从美国搬来的教学制度或方法。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人们”的理解未尝不是一种偏见,仿佛“中小学教师”做的事都是低人一等,或做不好“学术界”的事,忘了像钱穆这样的“中小学教师”甚至比学界中人还善于做学术,钱穆这样的“中小学教师”即因为学术出色,成为学术上能与胡适匹敌的一流高手。只是“中小学教师”钱穆的学术实践,从乡村小学时以《论语》文法研究来改革《论语》教学,到苏州中学期间写完《先秦诸子系年》、击破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谬说,都未曾发生在舒新城式的教育学家身上。舒新城式的教育学家只知道向中小学教育界介绍“道尔顿制”,如此自然会让“人们”以为教育学就是鼓动“中小学教师”实验教学法。
其实,几年努力实验下来让教育学被外界认为是“教学法之学”,结果并不算坏。毕竟十年前(即1914年),教育学在“人们”印象中似乎什么具体形象都谈不上,连陈鹤琴这样的决定要去美国攻读教育学的清华学子,都不知道这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只觉得“教育是一种很空泛的东西”。[17]64十年后,经过舒新城等教育学家的努力,教育学非常显著地表现为传播、实验“教学法”,也算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成绩。真正恐怖的乃是造成“教学法”改革运动之后,那些“借教育为啖饭之地的官僚政客、军阀流氓”也会混于其间。南北两路教育学阵容本就鱼龙混杂,又有这些人掺和进来,显然更会败坏“五四”以来教育学者的学术文化形象与声誉。不过,第二年(即1925年),“道尔顿制”运动作为“五四”以来教育学实践的著名典范,便突然失败了。东南大学附中校长廖世承更是公布实验报告,指出“道尔顿制”不符合“新学制”“班级授课制”等基本国情,只适合“学生人数较少”的“天才生班”或“低能儿班”。[18]174
二、何去何从:后“道尔顿制”时期的教育学
试验失败之后,发起“新教育运动”的一群教育学人不得不另觅学术生产新路。1925年之后的几年(至1931年),可谓教育学的低迷与危机时期。危机意识淡薄的教育专家和中小学教师尚会继续以“教学法”改革的方式来展现“五四”以来的教育学,而且“道尔顿制”发明人海伦·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也不明就里地赶来助阵。不过,“道尔顿制”本土代言领袖舒新城却彻底放弃了“教学法”改革。他后来回顾自家教育生涯时,甚至提醒世人记住,他的“道尔顿制”著作在其“教育著述以至于一般著述中都不占很重要的位置”。[12]359
放弃领导“道尔顿制”实验之后,舒新城仍会研究“教学法”,但它确实不是其主要的教育学实践形式,其主要的教育学实践形式乃是转向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并于1925年至1931年间,先后推出《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等教育史著作。[19]另一位重要的教育学家及“新教育运动”大将陶行知则毅然辞去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之职。陶先生认为,“五四”以来“新教育”理论不是“从主观的头脑里空想出来”,就是“间接从国外运输进来”,这两路教育学生产他都不想从事,他想根据自己对于中国乡村“国情”的“亲切体验”,发展中国急需的“乡村师范教育”。[20]644
日后,陶行知又依靠自己的“亲切体验”,成为备受无数难童爱戴的校长甚至父亲,成为反抗日本侵略,批判国内腐败当局的伟大斗士,其所作所为堪称整个教育界的骄傲,张申府更是将陶行知视为“最值得钦服”的“知识分子”。[21]6211925年以来,真正尴尬的是南北各路留守学院但不想继续研究“教学法”,又无法成为“知识分子”的教育学者。他们不想继续研究“教学法”,或是因为意识到了教育界的学术权威不认为“教学法”是像样的学术研究,或是因为自己也觉得研究“教学法”很难让自己在学院立足,而他们又不像陶行知那样在“国情”方面有太多“亲切体验”,并因此看淡学界位置与名声,成为学界之外担负国难的“知识分子”。
何去何从,的确十分尴尬。其中况味正如时任《教育杂志》编辑、曾帮助舒新城推出“道尔顿制研究专号”的周予同所言:“心意几乎无法统一,对于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感到难堪的苦闷”。[22]4周予同在北京高师求学时,曾是钱玄同的得意学生。1921年毕业后,因在《教育杂志》做编辑,周予同开始“从事教育学的研究”。除帮助舒新城推广“道尔顿制”外,他自己也发表了“十来篇”讨论“教育制度改革”的论文。但从1925年“道尔顿制”实验宣告失败起,他便回到了其师钱玄同以及同辈友人顾颉刚提示的学术路径,“把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经学史”。[23]
周予同其实还做过舒新城想到的近现代教育史,他的学术调整表明,1925年以来的教育学人除了“教育史”之外,其实还可以转向“经学史”,而且“经学史”更能赢得学界重视。虽然相比于陶行知,经学史也好,教育史也好,都远谈不上是当时“知识分子”应做之事,但对只能滞留学界的一介书生而言,这些选择毕竟多少也还可以丰富一下当时教育界的学术文化生产,周予同、舒新城也都因为调整学术生产路径,成为颇受重视的经学史和教育史名家。何况对1925年以来留守学界的教育学者而言,似乎也就只有往“史学”上靠,才有可能赢得学术权威们的学术尊重。
张彭春的一番暗自调整可以更深刻地说明这一点,即如果想让教育学超越“五四”以来的“教学法”样态,变成能够赢得学界认可的“学术文化实践”,就必须往“史学”上靠,而且必须往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北大、清华史学权威的路数上靠。张彭春生于1892年,1915年便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硕士学位,此后协助其兄张伯苓创办南开中学。1920年,张彭春再赴哥大师院,师从杜威,并于1922年获教育博士学位。据知情人胡晓风所言,当年年底,张彭春即回国,加入陶行知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负责“中学校课程改进的研究”。[24]
第二年,张彭春主持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北京高师联合举办的“中学课程研究班”,尝试把北京高师和北大教育科学子,以及北京各中学教员共60人,培养成“课程研究员”。张彭春之被北京高师聘为“中学课程教授”,或许就是在1923年。提及这些是为了说明,张彭春也许是“五四”以来教育界的第一位“课程论”教授。同时如陶行知所言,张彭春确实在“中学课程”领域做了不少“调查”、“改造和试验”工作。[25]385一定意义上或许还可以说,他在当时最流行的教育学——“教学法”改革——之外,开创了另一种教育学生产方式,即对“中学课程”展开“调查”,进而寻求中学课程制度“改造”之策。
然而1923年夏秋之季,清华学校决定筹办大学,并向办学有方的张伯苓请求支援。张伯苓便把其弟调往清华,担任教务长。之后,到1925年,张彭春为清华拟定了包括成立国学院、培训科学教师在内的诸多办学计划。但就在1925年,陶行知“估计到中华教育改进社将会自然消失”。后续演变的确如此,这意味着,张彭春在社中负责的“中学课程”调查与改造研究也将自然萎缩。与此同时,在清华主持教务的经历也让他对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教育界学术权威推崇什么样的学术文化有了切身体会。
和周予同、舒新城一样,1925年前后的张彭春也在学术上陷入了何去何从的尴尬境地。而且因为人在清华这一学术重镇,张彭春感觉到自己“国学程度差而常为同事所看不起”,更是迫切需要重建自身学术功夫。张彭春很清楚“中国所谓‘学’都偏重于史”,“现在公认的学问家如同梁、胡,也是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26]135-136到底是局内之人,很快便能摸清胡适、梁启超等当时主流学人的学术文化,那他如何向史学靠呢?张彭春想到的办法是从教育的角度“整理国故”。
他说:“先秦的名学,适之做过一度的整理。谁来做先秦教育的调查?”看来,他似乎想把此前的“调查”功夫用到“先秦教育”上,可惜由于所掌握的材料有限,无法进一步考察张彭春准备如何调查先秦教育,尤其先秦时期的“中学课程”是否在其调查计划之内,只知道他觉得自己“古书的底子太浅了”,[26]135无力做出能让胡适、梁启超等人器重的先秦教育调查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张彭春并不会因为“古书底子太浅”而丧失文化创造进路,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除了学教育外,还主修过“文学”,且尤其擅长现代话剧。
正因为还另有专业本领,1925年之后的张彭春在忙于行政与应酬之余,仍可以依靠自己的话剧创作,为整个教育界贡献诸多堪称史无前例的现代文化与新文化教育成就。1927年张彭春率先编导易卜生的名剧《国民公敌》,便是一显著贡献。胡适也喜欢易卜生话剧,但他似乎顶多只能率先在《新青年》上制作“专号”,向教育界宣传,张彭春则可以将这一现代文化展现在舞台上,让国人真切感受其中的思想力量。第二年话剧完成,“连演两天,每次皆系满座……会场秩序甚佳,演员表演至绝妙处,博得全场的掌声不少”。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张彭春仍能和其学生曹禺合作推出话剧《财狂》,再次“掀起热潮,郑振铎、章靳以、李健吾、萧乾等知名作家专程从北京赶来观看此剧”。[27]
转向话剧或者文学艺术,也可做出一番比“教学法”改革更有把握也更有意义的文化与教育革新事业,进而丰富教育界乃至文化界的“新文化”生产,张彭春的调整充分说明,除了向“史学”靠拢,开展能被教育界学术权威认可的学术文化实践外,1925年以来因“教学法”运动遭遇学术危机的教育学者其实还有另一条新生之路,它便是转向现代文学艺术创造,将教育学改造成胡适亦十分渴望却没有能力开展的“新文化”生产与“新文化”教育实践。当然这一转向的前提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专业基础,就像周予同之所以能转向经学史,得益于大学时的老师是章太炎弟子。假使一直都是只有杜威教育学这一种专业基础,显然就只能到中小学推行杜威一系的教学法了。
身为研究“中学课程”的教育学教授,张彭春恰恰因为同时具备文学与话剧专业能力,才得以成功转型,而且取得了令时人瞩目的“新文化”生产与“新文化”教育成绩。谁能想到,一位“中学课程教授”竟能有此“新文化”创造成绩和“新文化”教育贡献:不仅让南开中学成为“现代中国话剧”的发源地和话剧人才摇篮之一,而且还有一系列曾令整个文化界震动的现代话剧创造实践。
除张彭春外,也曾在北京高师担任教育学教授的萧友梅同样值得关注。和张彭春一样,教育学出身的萧友梅也有深厚的第二专业功夫,他的第二专业功夫便是音乐。1912年,已有教育学学位的萧友梅前往德国学习音乐、哲学等,八年后才回国,系中国第一位音乐学博士。回国后,萧友梅先是在北大创办音乐传习所,堪称蔡元培“以美育代替宗教”的重要实践者,然后又参与了当时的“新教育运动”。正因为还有深厚的现代音乐功底,萧友梅不仅不会陷入“教学法”实验的死胡同,而且在“新教育运动”退场之后,能够另外开辟文化与教育革新进路。1927年,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后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此成为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创作和现代音乐教育的缔造者。
萧友梅、张彭春均可以轻松突破一般教育学者以“教学法”改革为中心的实践方式,改以真正的“新文化”实践来创造“新教育”。遗憾的是,在“五四”以来的教育学界,像张彭春、萧友梅这样善于调整文化实践路向,又有文化实力作好调整的教育学者并不多见,而且教育界或文化界似乎也未把他们看成是教育学界的代表。同时,教育学界也没有把他们的“新文化”实践立为学术典范。总之,1925年以后的教育学在教育界的尴尬学术处境不会因为张彭春或萧友梅的文化与教育实践发生质变,不仅不会,反倒因为“五四”以来的诸多显著表现——学者阵容背景极为复杂,缺乏一流学者,在各地中小学实验“道尔顿制”等,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学术生存危机。
三、突遭厄运:教育学者的反思与自救
地理上离“新教育运动”与“道尔顿制”运动大本营最近的“学衡派”猛将胡先骕最先向教育学者发难,将杜威之中国弟子的老底抖出,直言后者皆是不学无术之徒,说他们就读的“赫赫有名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皆是收一些“哈佛、耶尔、芝加哥、霍布金士所斥退之学生”。其中的中国学生“平日于中西学术绝无根底,故除墨守师说如鹦鹉学舌外,别无他能”。胡先骕还以“北京师范大学同班之毕业生”为例,说“一入芝加哥大学须补习一年方能得学士学位,一入哥伦比亚师范院,一年即得硕士。”[28]言外之意,师范学院的学位实在太好拿。
胡氏所言未免有些刻薄,但并非全无根据。如美国本土史家所见,19世纪末,以哈佛为首的美国大学起初一直不想接受当时以研究“教学艺术”为主的教育学,后在地方教育当局劝说及进步社会运动鼓舞下,哈佛校长艾略特才勉强“答应给愿意到高中任教的人提供教育专业训练”。[29]225而且即使教师训练班后来发展成独立的教育系和教育研究生院,也很难招到学业成绩好的文理学院毕业生。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一些知名人文社会学者和文理学院高才生进入哈佛教育研究生院。[30]
至于20世纪初期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乃至全体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学术表现,同样容易让人诟病。除胡先骕不乏了解外,1919年时在哈佛的吴宓也曾指出,包括师范学院内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无以学问为正事者”,热衷于“两种职业”,一是“竞争职位,结党倾轧,排挤异党之人”;二是“纵情游乐,无非看戏、吃饭、跳舞、狎妓等事,而日常为之,视为正业。”相比之下,哈佛、麻省理工所在地“波城及其附近,亦有留学生百余人,然大率纯实用功、安静向学者居多”。“哈佛及麻省理工学院,课程亦较严,迥非纽约哥伦比亚等校之比。而纽约之中国留学生则鄙夷之,谓凡来波城之读书者,皆愚蠢无用之人,不如彼辈之活动能事。”[31]60,70胡先骕作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生的知情人,出来兜老底,的确大有文章可做,很容易揭穿归国教育学者的学术根底。
接着,1929年,汪精卫一系的政论家陶希圣也在《教育杂志》的首篇位置上发表论文,教“教育学家”如何做教育史研究。而且《教育杂志》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教育专业刊物之一,竟会允许“政客”作者一上来便不无得意地说:“本文是历史学的教育论,不是教育学的历史论,……以此占领教育杂志的篇幅,而呈示于教育学家的前列,作者实报无限的歉意”。[32]所言是否只是客套,这里不得而知,但“政客”作者确实应该向“教育学家”道歉,哪有这样来戏弄的,完全不顾自己并非造诣一流的史家,却以史家自居于“教育学家的前列”。当时《教育杂志》的准入标准怎么就做不到像《国学季刊》或《清华学报》那样高呢?哪怕像《燕京学报》那样高,或许也不会有此闹剧。
难怪连很少卷入是非的陈寅恪都会看不下去,以至于在1931年清华二十周年校庆典礼上,,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33]361将“多数教育学者”视为“政客”,或许有欠公允,但当时的教育学者又拿什么来打破学界成见呢?然后,教育界的“学霸”傅斯年也开始发炮,将三十年代初的“教育崩溃”与“哥仑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毕业生给中国教育界的一大贡献”联系以来,认为“五四”以来兴起的教育学乃是造成“教育崩溃”的一大原因之一。
傅斯年还问胡适,为何“这学校的中国毕业生,在中国所作所为,真正糊涂加三级”,胡适说“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个小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之后,傅斯年对教育学者的表现做了一番评价:“这样说来,是学非所用了,诚不能为这些‘专家’叹息!这些先生们多如鲫,到处高谈教育,什么朝三暮四的中学学制,窦二墩(即道尔顿)的教学法,说得五花八门,弄得乱七八糟。”傅斯年认为,“小学,至多中学,是适用所谓教育学的场所,大学是学术教育,……教育学家如不于文理各科之中有一专门,做起教师来,是下等的教师,谈起教育——即幼年或青年之训练,是没有着落,于是办起学校来自然流为政客。”[34]8-10
句句几乎都是为了将教育学从学院清除出去。面对傅斯年的猛烈炮轰,邱椿率先站出来代表教育学界做了三点反击。首先,傅斯年“未免太看得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毕业生,实际上,他们在教育界的势力远未大到需要为“教育破产”负责。其次,“欧美各大学其他学院的中国毕业生”同样不乏“不学无术”者。最后便是最关键的一点,即教育学可否与文理科并列为大学的独立学术。对此,邱椿自然持肯定观点,理由是“美国省立大学与著名私立大学的教育学院与文理学院都处于绝对平等的地位”。[35]
前两点反击当无异议,但后一点论据则明显站不住,即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师范学院恰恰“不被视为一所与其他学院平起平坐的学院”。[36]27当然,对双方而言,事实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论辩双方均无法冷静下来去详查实际情况,而是陷入了相互排斥、指责的紧张境地。傅斯年认为,“五四”以来的教育学实践把全国教育“弄得乱七八糟”,又说教育学者“办起学校来自然流为政客”,未免皆是气愤之语。邱椿出来反驳同样是因为“恼羞成怒,腔子里堆积许多话不能不借个机会倾吐出来”,以至于情绪性地反讽傅斯年推崇的现代“考古学”也算不上值得教育学者认可的学术——“假若不懂‘挖坟墓,嚼枯骨’的中国考古学便算不学无术,百分之九十九的师范学院毕业生都会毫不迟疑地自认为是不学无术之人。”[35]
收到邱椿的反击,傅斯年又作了回应,语态稍显客气,希望教育学者注意两点:一是“师范学院的中国毕业生确曾在中国民七八以来的教育学界占一个绝大的势力,而其成绩我们似乎不敢恭维”;二是“先有一种文理专科之素养,再谈教育,方是实在的,否则教育学虽有原理,而空空如也。”[37]很明显,邱椿及教育学界与傅斯年所代表的整个教育界的学术权威之间,已经无法调和。而且1925年“教学法”运动退场之后,即使教育学界能够调整学术生产,也来不及了。两年后,即1927年,“五四”以来以“教学法”实验为主的教育学开始遭遇被主流学界扫地出门的“空前厄运”,连学院一席之地都难以保住。如邱椿1932年所见:
近五年来,教育学在中国遭遇空前的厄运,因此学教育学者也大倒其霉。少数有权威的学者,不但不承认教育学为一种“科学”,而且不承认教育学为一种“学科”。清华大学的教育系取消了。武汉大学本是武昌师大的后身,但改大后不但无教育学系,并且文学院内也不设教育学讲座。广东中山大学亦是广东高师所改,也不设教育学院。最近青岛大学——山东大学——的教育学院停办了,中央大学的教育学院的规模也被缩小了。于是,学教育学而希望当教授者都有“绕树三匝,何枝可栖”的感慨。[35]
学院体制境况如此悲惨,还要被人落井下石,强加罪名,难怪邱椿会“恼羞成怒”,奋起反击“学霸”。但愤怒与言辞反击显然不能让教育学走出败局,而必须检讨、革新“五四”以来的所作所为,方可能赢回学院一席之地。就此而言,赵廷为之后的反思颇值得注意。相比于邱椿的愤怒与反击,“教学论”专家、《道尔顿制》译者赵廷为则务实地把自己的反思主题转换为“教育的学问为什么给人家瞧不起”,并以笔名撰文,在受众面更广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2号,1933年1月16日,“教育栏”,第3-9页)检讨错误,呼吁教育学界正视日益严重的学术危机处境,积极思索学术革新之路。
赵廷为认为,关于“为什么人家要瞧不起教育的学问”,“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我国研究教育的人们——连我自己在内——都太不争气,……所以人家就连带的把我们所研究的教育的学问也看得一个钱不值得了。”由此可贵的虚心自责出发,赵氏批评了当时教育学者的四大“弱点”,其中“最大的弱点就是一味的学时髦。他们今天讲道尔顿制,明天讲测验。在时髦的时候大谈而特谈,等到不时髦的时候,就闭口无语”。其他三大“弱点”包括“太会适应环境,与不学教育的人一样党同伐异,……抢地盘和利用学生”;“对于学问方面不肯下苦功夫”;“研究的兴味实太狭隘”。[38]
列举完四大弱点,赵廷为希望教育学者“除满足求生的冲动外,还应该分出一部分的精力,努力于各种教育问题的真实的研究”。赵廷为认为,就当时情况而言,教育学者应努力研究“中国卑怯的民族究竟怎么会造成”,“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中国卑怯的民族改变而成强大的民族”,教育怎么“救国家救人类”,怎么改变“中国学生的无纪律”。这便是赵廷为为三十年代初病入膏肓的教育学开出的学术重建药方:教育学者应致力于生产“国民性改造教育学”、“救国教育学或救人类教育学”以及“学生纪律教育学”。[38]
无疑,赵廷为依然是从狭隘的教育学视野出发考虑教育学重建,没有想到鲁迅这样的新文学先锋十几年前便已通过小说、杂文创作,贡献了力量强大的“国民性改造教育学”,更未考察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各路学术权威的学术文化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教育学怎么可能达到当时的学术认同标准。至于1925年以来舒新城、陶行知、张彭春、萧友梅等几路“教育学教授”的学术文化调整努力,同样不在赵廷为的反思视野里。视野依然被狭隘的教育学束缚,即使生产出了“国民性改造教育学”一类的“新教育学”,恐怕也还是无法在学术界和文化界确立教育学的学术文化尊严与价值。
由此或许还可以认为,赵廷为式的反思尽管十分务实,也非常虚心,但其一番重建构想似乎只是表明,教育学自身其实早已失去能够挣得学术文化尊严的学术视野与学术活力,因此无论怎么重建,或许都无法赶上学术界及文化界的“新文化”生产与“新文化”教育步伐。这些当然都是事后之见。不过到40年代,教育学仍未翻身成为备受学界尊重的学术文化专业,亦是不争之实,乃至钱钟书在《围城》里刻画四十年代教育界种种怪状时,无需考证便可来一句:“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39]78-79
钱先生有无讽刺教育学的意思,不得而知。但这样的话及其背后反映的学术舆情,的确又会令教育学感到难堪。还好,这里尚可以顺着钱先生的叙事宗旨做点发挥:其实,理科、文科也好,文科内部也好,皆没有必要互相瞧不起,因为谁也强不到哪里去。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考古学院士的夏鼐便曾提醒教育界同仁不要忘记“中国学术的根基极浅,尤其是自然科学可以说刚是萌芽”。[40]5的确如此,,叶企孙等科学教育家自1925年起辛苦耕耘出来的“萌芽”才开始收获能与西方强敌较劲的现代科学成就。
文科方面,何尝不是如此。朱自清便曾坦言,四十年代教育界的文科学术成绩还不如1937年以前。[41]490-495当然,夏、朱两位先生都是从学术文化角度来衡量。,则大可以认为,。仅以音乐教育界为例,,,并创造了许多提振民族士气的救亡歌曲。[42]因此,这当中最重要的其实仍是克服所谓派系纷争或“文人相轻”的无聊毛病,同时不被西方文化牵着鼻子走,努力为整个教育界与国家创造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教育。
末尾想说的是,今天的教育学正在如何组织学术生产,其学术文化成绩在学术界居于何种位置,为整个教育界及国家贡献了什么有益的“新文化”,均不在本文的考察之列。不过,本文叙述的教育学兴衰往事显然能为探讨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样说,自然是希望当代中国教育学界能够回望“五四”以来教育学的所作所为,尤其当出现学术认同危机的时候,能够重识舒新城、陶行知、张彭春、萧友梅等昔日各路教育学前辈如何重建自己的学术文化实践,从而提高教育学的学术文化品质。如果还能像张彭春、萧友梅那样,发展现代戏剧或音乐等“新文化”创造及教育实践,那当代教育学者便也可以直接为国家,为学生,为社会贡献优秀的“新文化”了。
参考文献:
[1]丁钢. 20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一份博士名单的见证[J].高等教育研究.2013, 5.
[2]周洪宇,陈竞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现代中国教育[J].比较教育研究.2010, 11.
[3]陶行知《杜威将来华讲学——致胡适》,《陶行知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陈文彬.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挟洋自重”[J].书屋.2006, 7.
[6]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M ]//鲁迅.三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7]张小丽.北高师教育研究科的历史境遇[J].教育学报,2011, 4.
[8]周晔.〈新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J].高等教育研究,2005, 1.
[9]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三联书店, 1998.
[11]舒新城. 蜀游心影[M].上海:开明书店, 1929.
[12]舒新城. 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5)[M].上海:中华书局,1945.
[13]舒新城.现代教学方法[M].上海:开明书店,1930.
[14]胡适.书院制史略[G]//胡适学术文集·教育.北京:中华书局,1993.
[15]王建军.盲目趋新与教学改革——舒新城对道尔顿制教学实验的忧虑[J].课程·教材·教法,2005,(5).
[10]崔运武.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1994.
[16]叶澜.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J].教育研究,2004,(7).
[17]陈鹤琴.我的半生[M]//胡适,,陈鹤琴.四十自述·我在六十年以前·我的半生.长沙:岳麓书社,1998.
[18]廖世承.东大附中道尔顿实验报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19]易琴.20世纪新教育运动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的兴起——以舒新城为个案[J].教育学术月刊,2011, .
[22]周予同.现代中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
[23]周予同.周予同自传[J].晋阳学刊,1981, 1.
[20]陶行知.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G]//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21]张申府.这打击得了民主运动么——怀念韬奋先生,痛悼陶行知先生[G]//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24]胡晓风.张彭春等: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J].生活教育,2011, 3.
[25]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社务报告》的补充说明[G]//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26]罗志田.日记中的民初思想、.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7]郭武群.张彭春对中国话剧的三大贡献[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2.
[28]胡先骕.师范大学制评议[J].甲寅,1925, 1(14).
[29]Buck P.The SocialScience at Harvard,1860-1920[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30]周勇.动荡的学科与专业——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的百年难题[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 2.
[31]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2]陶希圣.中国学校教育之史的观察[J].教育杂志,1929.21(3).
[33]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与清华之职责[G]//陈寅恪,陈美延.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34]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G]//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35]邱椿.通信[J].独立评论,1932, 11.
[36]O’leary T F. AnInquiry into the General Purpose,Function,and Organization of SelectedUniversity Schools of Education[M]. Washingt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Press,1941.
[37]孟真.答[J].独立评论,1932.30(11).
[38]轶尘(赵廷为).教育的学问为什么给人家瞧不起[J].东方杂志,1933.30(2).
[39]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0]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第1辑[Z].南京:中央研究院内部发行,1948.
[41]朱自清.论学术的空气[G]//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42]胡然.发刊词[J].音乐学刊,19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