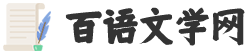多年前我读王元化和林毓生的通信,当他们谈到关于文化的衰败和人的精神素质下降,我就认同了他们的感叹,“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只是,我心里还有不甘,总觉得世间万事原非定局,它是可以变的;人力虽然渺小,但也是可以增长和积蓄的。
by-谢有顺
不仅记得,还要晓得
文 | 谢有顺
我是很早就给自己定了原则,不写序、不上电视的,所以去年有师长约我为学生的优秀毕业论文集写序,我便婉辞了;今年再约,居然不好意思推脱,答应了下来。
我忽然想起,曾有学生说我对博士生严苛,对本科生却是很好的。这大约是真的。许多的博士生,定准了要以学术为志业,早早就为知识、规范、成果所累,心灵已无多少伸展的空间,一切似乎都格式化了,所以,一本本厚厚的论文读下来,得到的印象无非是认真、规矩二字,几乎没有多少旁逸斜出、生机勃勃的段落。论文的写作,普遍成了关于某个问题的枯燥推演,或者成了一种知识谱系学的梳理,而不再是牟宗三所言的“生命的学问”。
我经常问学生,你喜欢谁的作品?喜欢研究哪些问题?他们往往答不上来。
哦,原来他们并无喜欢,写作和做研究,不过是完成任务而已。
没有喜欢,没有个体生命的投入,文字就定然不会有体温、有文采,学问就更谈不上能贯通天地和人心了。钱穆说,凡做学问,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具备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
但今天的学问,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今天的文学,也几已成了“纸上的文学”。身世和时代正在消隐,所剩的,不过是些材料、名词、公共经验,以及下面那颗斤斤计较的心。
,“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我不是学问家,但也知道,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仅仅为知识所累。
所谓“学”,本义当为觉悟,而“术”是道路、是方法;学术,其实是一种觉悟的方式,学者则是正在觉悟的人。在学问之中,如果不出示觉悟之道,不呈现一颗自由的心灵,那终归是一种技能、工具,是一种“为人”之学,而少了“为己”之学的自在。
所以,我每年阅读论文数以百计,心为之所动的时刻,却是太少了,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不再对学术的快速生产抱太大的希望。事实上,多年前我读王元化和林毓生的通信,当他们谈到关于文化的衰败和人的精神素质下降,我就认同了他们的感叹,“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只是,我心里还有不甘,总觉得世间万事原非定局,它是可以变的;人力虽然渺小,但也是可以增长和积蓄的。
这也是我对本科学生怀有更大的热忱,对他们写的论文抱有更多好奇和期许的原因之一。
他们年轻,充满活力,身上还有不愿被压抑的梦想和激情,还有未被现有教育方式损伤的直觉和率真。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在论文写作中还不知如何“达之于道”,却也本能地拒斥着为学术而学术的孤冷。他们遵循规范,但也向往带着镣铐跳舞;他们仰视前辈,但也不忘自己发声。所以,在论文的一些段落,你总能发现他们的机智和会心,有时还杂着狡黠、幽默和过于大胆的臆断——这些看起来是最不整饬的部分,恰恰是这本优秀论文集中最见才华、最见性情的地方,它所塑造的是这一届学生的心灵底色,里面埋藏着他们的学术理想,也昭示着他们不同凡响的创造精神。
我尤为珍惜这些异质的思维和心得,因为有感而发比堆砌材料重要,摆脱历史束缚的能力有时也比历史感重要。
这些学生,一方面是秩序的囚徒,另一方面也应是反抗秩序的先锋——在他们理应放怀大笑的年龄,我们不该只看到他们脸上的肃穆和规矩;在他们还可以怀疑一切的岁月,我们更要学习欣赏他们的勇气和偏激。他们读书,写作,做研究,不过是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而已,至少,我在指导学生的时候,会尽量呵护他们的这种个性和激情。
我一直记得《传习录》里的一段话,“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这个自家本体,就是“活泼泼的”心性,也是胡兰成所说的“不失好玩之心”,照王阳明的意思,“此是学问极至处”。王国维赞李后主的词“不失其赤子之心”,鲁迅称《红楼梦》为“清代之人情小说的顶峰”,又何尝不是对一个作家那“活泼泼的”心性的盛赞?
大学四年读下来,同学们这种“活泼泼的”心性还残存乎?多数的时候,我对当下教育境况是悲观的,除了大才可以在任何环境下拔地而起以外,更多的人,不能不受时代风潮的感染,也不能不在学业、就业的压力下而妥协,而世故起来;他们的忧虑和危机感,在塑造他们的参与意识的同时,也在删除他们内心里那些多余的枝蔓——尤其是“活泼泼的”部分,慢慢的,就只能深藏于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了。
因此,当我和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漫谈时,话题也开始变得世俗而具体,他们尽管还保留着对文学的敬意,对校园的眷恋,但目光已经很少在其上逗留,他们似乎更向往那种面对社会的成熟。看得出,他们正在掩饰自己的活泼,正在使自己目光深邃。
所幸,还有这本优秀毕业论文集摆在我的面前,作为一种记录,既是这些学生心灵的私语,也是他们智慧的痕迹,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他们不仅“记得”,也还“晓得”,甚至还有些许的“明得”——论文中这些真正有价值的、“活泼泼的”觉悟之思,被淹没在词语的海洋中时,未必醒目、未必集中,但它们却是我读之最难忘怀的部分。
所谓优秀,此之谓也。
— END —
编辑︱诗人 文君
/ 延 / 伸 / 阅 / 读 /
《成为小说家》
谢有顺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版
相关阅读
谢有顺 | 孙绍振老师并不幽默的一面
谢有顺 | 史铁生:一个尊灵魂的人
谢有顺 | 批评是一种有思想的艺术
谢有顺 | 认识一个文学岭南
谢有顺 | 中国当代文学的有与无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