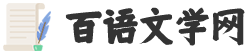王文智. 课程研究因何叙事?——基于三段课程学术历程的考察[J]. 全球教育展望, 2015, 12.①
摘要:在课程研究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康纳利、派纳和古德森作为“课程开发”、,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研究问题出发,最终都走向了叙事研究。本文对他们转向叙事的学术历程进行考察后发现,叙事能够帮助课程研究从容应对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摆脱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的依赖,延续本领域的学术传统,直面学校情景中的教育经验,找到适合自身的理论方式。
关键词: 课程研究;教育叙事;课程史;概念重建
作者简介:王文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博士后(上海 200062)
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课程研究的分化
20世纪70年代西方课程研究实现了从“课程开发”向“课程理解”的范式转换[1],如今这段历史在课程领域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具有“反理论”性格的课程开发模式将课程领域引向了施瓦布所说的“垂死”境地[2]。而施瓦布关于“课程领域已岌岌可危的声明标志了概念重建十年的开始”[3],概念重建运动给这个领域带来了理论上的繁荣。
然而,课程学术发展的这种历史叙事里却包含着自相矛盾的地方。施瓦布在他那一系列被看作开启“概念重建”时代的论文里期盼的,恰恰不是理论的建设,而是实践的艺术。他明确地要求课程领域将其力量“从对理论的追求上移开”[4]。而被指责具有非理论倾向的泰勒,却早在1950年(当时他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刚刚出版)就与赫里克(Herrick, V.E.)合作撰文强调课程理论建设的重要性[5]。正如赫莱伯威茨(Hlebowitsh, P.S.)所说的,在1970年代人们对课程领域的状况进行反思时,泰勒的工作曾被误解甚至是歪曲了[6]。即便泰勒原理、“目标模式”所展现的程序性特征和“技术理性”,确实不足以支撑课程理论的多元发展。但真正扼杀课程研究创造力的,并非泰勒等人的课程开发模式,而是之后二十多年中研究者对泰勒体系程式化地固守。让“泰勒原理最著名的批评者”克利巴德(Kliebard, H.M.)感到不满的,也不是泰勒原理本身,而是后来者们躺在泰勒原理上停滞不前了太久。克利巴德曾指出,在课程领域,不论由谁来立一间什么样的宗庙,“泰勒原理都应被供奉于神龛之内”[7]。泰勒真诚地认为课程研究者应该在教育实践中与教师和管理者们通力合作,为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而努力,他的视野是广阔的。
但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推出之后,对课程目标的“窄化”②,对技术和效率的过分强调,却代替了对学校教育目的的全面考量。特别是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后,美国公众对学校课程的质疑,以及随后的国防教育法案,彻底改变了课程事务的格局。原本与课程学者紧密合作的地方教育管理者、校董会和教师们所拥有的课程权力,被转移到了以科学家们为高参的联邦政府和各种基金委员会的手里;新的课程变革采用的是关注国家竞争、军备竞赛、尖端知识和卓越人才的一整套逻辑,肯定儿童个人生活的价值、建设民主社会新秩序等诉求都被舍弃了,“对学科的探究代替了对自我的探究;对知识结构的理解变得比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更重要;关于学习的理论变得比关于知识的理论更有价值。”[8]泰勒曾系统地总结了前人寻找课程目标的三大来源,学生、社会和学科,而到这个时候被强调的却只有学科,目标和内容都是既定的,不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课程人可以用良知和智识发挥引领作用的所在。布鲁纳(Bruner,J.S.)的《教育过程》是统领1960年代的课程宣言,这位心理学家在书中写道:“这一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有效地呈现学科知识”。[9]
课程领域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此时也被改变了。此前,课程专家更多地通过自己在学区和学校里的专业实践获得理论认知;此后,他们一定程度上退化为心理学理论的应用者。此前,课程专家既服务于教师,又引领教师和他们一起寻求变革和进步;此后,其中的一部分人却要去开发“防教师”(teacher-proof)的课程。一些课程学者的研究开始和学校教育情景相脱离,这便是施瓦布所批评的远离实践的课程理论研究。
因此“概念重建”这一代课程学者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告别理论转向实践,也不是埋头书斋远离实务,而是汲取新的学术资源让这个被窄化的领域重新丰富起来,在追求理论创新的同时,以崭新的视角关怀实践。由此,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塌缩之后,课程研究的问题域再度扩张。然而这种扩张也使得课程领域陷入了严重的“巴尔干化”。“概念重建运动”结束后,课程研究者们遵循着不同的研究范型,使用着迥异的理论话语,看起来是各做各事、互不相干。领域中有忠于“课程开发”的传统阵营与概念重建阵营相对垒,,。分歧无处不在,似乎没法找到任何共同点。1970年代末,“课程开发”的代表人物坦纳夫妇在观察概念重建阵营的研究之后,感慨这些人“仿佛来自另一个国度”[10],而今天不同研究取向的课程学者之间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则更为强烈。
二、殊途同归:三段课程学术之旅
然而无论课程研究成为一个如何开放且多样化的领域,其中的研究者们都需要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积聚力量,共同应对领域内外不断浮现的各种挑战,而不是各说各话、互不往来。[11]那么,承袭“课程开发”、,在概念体系和方法程式等方面是否完全没有共通之处?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的国际课程研究中,叙事已经成为不同派别的研究者都能够接受的开展探究和呈现成果的方式。那么,原本在课程领域中并不常见的叙事研究,是如何进入学术话语的中心,并成为不同派别的课程学者对话和共进的一个基点的呢?我们不妨从“课程开发”、,看看他们与叙事研究之间的“纠葛”。
(一)康纳利:从科学知识到“教师实践知识”
康纳利(Connelly, M.F.)曾是一名科学教师,在中小学和大学里都有开发课程的经历。196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拿到了博士学位,在此前后一直在导师施瓦布和他本人都很熟悉的领域——科学课程与教学——当中辛勤地耕耘着。彼时康纳利的研究明显留有“学科结构运动”的烙印,是一位带着“学科专家气息”的课程开发者和研究者。他思考最多的是像“如何结合‘内稳平衡’、‘结构-功能’等生物学科基本原理来引导学生展开科学探究活动?”这类问题,其关注的焦点离不开“结构”和“探究”这两个施瓦布反复讨论的关键词[12]。导师对康纳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康纳利提到“探究”时都倾向于用“Enquiry”而不用“Inquiry”,这正是施瓦布的习惯。
1969年施瓦布宣称课程领域“将死”以后,在领域中酝酿已久的对研究现状的不满,终于汇聚成一股集体反思的热流喷发了出来。康纳利此时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课程开发”在研究和实践方面的问题。不过和那些在批判过后彻底放弃“课程开发”的人不同,康纳利仍然把课程开发活动作为自己摸索研究新路的出发点。
康纳利认为,“课程开发”工作失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专家学者主导的“自上而下”与一线教师主导的“自下而上”这两条路径之间来回摆动 [13]。类似施瓦布对理论和实践之差别的探讨,康纳利对课程专家和教师的工作逻辑作了区分。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着眼点,研究者往往考虑的只是解释某一方面的问题;然而教师开发课程时却不得不考虑方方面面的制约再做决定,教师的行动全是从具体的学校情境出发的。康纳利对这两种工作的差异做考察,不是要论孰优孰劣,而是要寻找分工合作的可能。在目标、起点和方法三个方面,外部开发者和教师都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在课程开发中发挥不同的功能。研究者的功能不是决定、指挥和控制教师,而是为他们提供合理的备选方案;教师的功能是基于学校和课堂的具体情境,审慎权衡并作出选择。康纳利发现,集权的、自上而下的课程开发路径的问题在于,教师往往没有很好地实现课程开发者的意图。[14]比如学科结构运动当中,很多教师以为自己完全接受了课程开发者的思想,但实际上教师们和专家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差别极大。课程项目的成败取决于使用者在学校和课堂的具体情景当中所做的决定,而做决定就意味着对开发好的课程进行改变。康纳利认为先前的课程开发者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师的作用(显然这也是对他自己以往工作的反思),在和几位中学科学教师合作开展课程开发的案例研究之后,康纳利提出“教师是在课程开发当中做出选择的人”[15]。
康纳利指出,在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得出的(事实性)原则,和教师实践中的(价值性)选择之间,无法画上等号[16]。既然教师是课程的最终决策者和实施者,那么对教师实践知识的探究或许比对学科知识研究更有意义。康纳利和他的学生克兰迪宁(Clandinin,J.D.)这样总结道,“我们相信,教师的‘个人知识’决定了课堂行为的意义……‘课程是什么’和‘我该怎么做’的问题可以通过教师个体的‘个人知识’而紧密地连接起来。”[17]
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后来成为康纳利和克兰迪宁一系列研究的中心主题。据两人自述,是在施瓦布、杜威乃至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论述的启发下,他们顺着“教师作为选择者和决策者”、“教师对理论的个人化运用”这条探究路径一路前行,[18]从而开启了对个人实践知识的研究,以及为他们带来世界性学术声誉的“课程叙事探究”。可以说,康纳利的课程研究之所以会走向叙事,离不开他对课程开发和课程改革的反思:“在传统的课程改革中,始终存在一种专家学者和师生之间无休止的张力。专家学者指令课程中应该教什么,师生被排斥在外却最终要经验这些课程……此书提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它强调每位教师在课堂里的个人知识的合法性。”[19]“课程改革的本质在于课堂里故事的互动。”[20]
康纳利和他的学生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中小学校里,同校长和老师们呆在一起,去理解他们的想法,参与他们的“仪式”[21](Rituals)、感受他们的“节奏”[22](Rhythms)、分享他们的“图景”[23](Images)。在研究教师的实践知识时,康纳利们极力地避免用课程学者自身的专业知识来框定和丈量,避免将教师的认知“抽干”成几个“在理论的层面”似乎了无新意的观点,而是尝试结合他们的工作情境和个人生活经历,完整地理解其经验。
在学科结构运动当中,康纳利将“科学家们在做什么?”作为思考科学教育的关键。因为理解了创造和使用着一门知识的人,也就拿到了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同样地,在思考教师们面对的课程与教学问题时,康纳利会对教师们说:“研究课程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研究我们自己”[24],“所有教和学的问题(所有课程问题)都应该站在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25]也正是为了理解参与者们和他们的经验,康纳利和克兰迪宁走向了叙事探究。他们两个“并不是从经验叙事的视角开始的”,为了“用更直觉的方法去顺应课堂中的生活、学校的生活以及其他教育情境中的生活”,他们“挣扎了好多年”。[26]在1980年代初一位哲学家将麦金太尔(McIntyre)的叙述整体性的概念介绍给他们之后,两人终于“找到了”叙事探究,并再也没有离开过它,因为“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的时候,就是叙事地思考”[27]。他们相信麦金太尔的观点,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28]。
回顾康纳利漫长的学术生涯,用“延续性”(continuity)这个他常用的词语作为注脚也许是恰当的。延续性不仅体现在他自身研究的自然演变,也体现在他与导师间、与学生间的代际传承。而接下来我们要考察的这位学者,则多少以一种与前辈的课程研究相“决裂”的姿态站上学术舞台的。
(二)派纳:“从内部入手”
相比康纳利,派纳(Pinar, W.F.)走向叙事的过程直接得多,尽管他不太使用“叙事”这个词。“自传”是这位概念重建的旗手理解课程的最主要方式。在派纳眼中,他和格鲁梅特(Grumet, M.)、米勒(Miller, J.)等人倡导的自传研究是“概念重建运动”的一翼(另一翼是阿普尔(Apple, M.W.)、吉鲁(Giroux, H.A.)和麦克拉伦(Mclaren,P.。他们三位和休伯纳(Huebner, D.)、范梅兰(VanManen)等人可称得上是“现象学-美学”取向课程研究的主力军。
派纳希望学校中的人们通过叙述自己的故事来重新发现“个体”,在《健全、疯狂与学校》一文中,派纳批评传统的学校教育让人依赖他人,迷失于他人之中,疏离自我,丧失自爱与自主。他写道,“我们毕业了,拿到了证书却没有清醒的头脑,知识渊博却只拥有人类可能性的碎片”[29],并提出教育理论家们需要进一步关照个体主体性。写下这些文字时,派纳只有25岁,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并开始在罗切斯特大学工作,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不少是源于对自己学生时代经历的反思。而作为一名教师(派纳在成为大学教师前在中学里教过两年英语),派纳并不喜欢预先设定行为目标再一板一眼地围绕目标教学,他在“走进教室的时候经常没有预想的教案”[30],只有“要教什么和结果将会如何的总体想法”,他带着学科知识、关于学生的知识以及他愿意分享的自我知识走进课堂,把自己和学生都作为一种“存在”,真诚地袒露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回应学生。派纳认为有时候他和学生们“并不怎么需要外在于我们的学科内容……我们从内部入手”[31],让学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内部世界”。
在派纳看来,“在通过集中注意于外部来理解教育本质的方法方面,我们已经走得足够远了。并不是公共世界——课程材料、教学技巧、政策指示——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为了进一步理解它们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必须把目光从它们身上转移开一段时间,开始漫长的、系统的对内部经验的搜寻。”[32]于是派纳在讨论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意识流小说对人之“内部经验”的探寻后,开始在自己的课堂上尝试一种新的方法,他写道:“我想使用的探究顺序关注着上述这些领域所关注的事物,但却并不完全照搬它们用以关注的方法……我们需要明确地找到这些方法的一些综合,以提供给我们一种独特的教育探究方法”。[33]于是年轻的派纳开始在罗切斯特大学的课堂中同学生们③一道探索这种被称为Currere(“课程”Curriculum一词的拉丁词根,其意为“跑”)的方法。在我国,Currere通常被译为“存在体验课程”,它是对教育经历的自传式反思。派纳提出Curerre主要包括“回溯-前进-分析-综合”[34]四个阶段,用类似心理分析中的“自由联想”方法从个人生活或存在经验这一“数据源”当中获取“数据”,然后用类似于现象学中的“悬置”的方式去思考它们,去检视自己的生活史。相比其他心理分析活动,Currere关心的是教育经历,同时Currere本身又可以构成一种教育经历,它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学校教育太注重用外部的、管理的、科层制的理性标准去审视学生,关注的是个体对“学生”这一社会角色的扮演,是客体化了的个体,Currere则让个体收复自己丧失了的主体性。
派纳认为“知识产品的质量和内容与理论家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理论家对他或她工作的传记意义的检视是非常重要的。”[35]因此他对自传方法的探索,既包含他对自己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反思,又展现了他对整个课程领域知识生产状况的忧思。由于与原初经验相疏远,依靠被理论概念限定住的次级经验,课程领域变得贫乏而缺乏想象力。尤其是当我们想关注课程当中的人时,可用的语言只有“科学的”语言,一种追究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语言,这满足不了派纳描述独特性、主体性和自我认知的过程的需求。因此“怎样使自己摆脱抽象的语言,怎样主观地写作”[36]成了派纳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对个人经验展开叙事,则是拟补理论语言之匮乏,摆脱“叙述紧张”的绝佳途径。[37]
虽然经常叙事,但派纳较少使用“叙事”一词,在《理解课程》中,他将康纳利和古德森等人的叙事研究都划归“把课程理解为自传/传记文本”的旗下,认为他们都属于“自传与传记研究的流派”[38]。使用哪一种旗帜其实无关紧要,即便侧重点不同,这些叙事研究之间的亲和性是没有人会否认的。
(三)古德森:从科目史到生活史
,古德森(Goodson, I.)无疑可以归入前一阵营,不过他是在英国成为国际知名的课程学者之后才来到北美的。古德森1943年诞生于英国一个不富裕的工人家庭,其早期的求学生涯都在英国度过。1970年,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古德森曾短暂离开大学,到一所综合中学里任教,因为他觉得在那里能直接地帮助贫寒子弟获得好的教育。然而当感到学校里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深受一些结构性因素的限制后,古德森回到高校院墙里,开始了他的课程研究。他从自身的教学经历中发现,对大多数学生们而言,一些贴近下层儿童的生活的课程很有意义,但这类课程的生存总是受到威胁。而那些在学校中地位稳固的学术性科目给学生带来的感受则并不愉悦,因此他将学校科目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为什么学校里要教这些东西,而不是别的。古德森深受英国“新教育社会学”,特别是伯恩斯坦和麦克•扬等人的研究的影响。。
古德森起初将自己对学校科目做的历史考察看作是课程社会学的“案例研究”,目的是用历史实证研究检验和修正现有理论[39]。古德森认为,以《知识和控制》论文集为代表的“新教育社会学”从权力的角度对知识的选择和组织背后的假设进行考察,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不过伯恩斯坦等人比较注重理论的建构而缺乏对具体事实的考察,没能详细地描述强势群体在定义学校知识的过程中如何对弱势群体施加控制。为此,古德森自己披荆斩棘开拓新路,研究学校科目获得合法性地位的历史,并引领了一批学者开展科目社会史研究,展现科目形成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和斗争。将优势阶层的知识占据学校课程空间的具体历史过程描绘清楚,也是当时北美批判课程研究必须面对的理论课题。单纯依靠宏观的理论分析来揭示优势阶层对学校知识的操控,并不足以让人信服,包括阿普尔(Apple, M.)在内的北美课程学者也意识到了开展历史研究[40],直面具体经验的必要。因此古德森的课程史研究在英美课程理论界取得了非常广泛的学术影响。
由于以检验和修正现有社会理论为目的,古德森早期的研究成果在形态上更接近社会科学当中的一些实证研究,采用了结构性极强的书写方式,论文分为研究意义、拟检验的假设、研究对象、新的解释框架和结论等部分[41],历史叙述也相应碎片化。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古德森抛弃了这样的研究和书写方式,转向人类学的、民族志的乃至传记的描述,开启了教师生活史的探究,引入了大量访谈和日记等材料,完整连贯的叙事成为他呈现自己研究的主要手段,乃至最终他将叙事研究作为自己最着意寻求突破的领域。
这是因为古德森发现,当研究面对一个具有延续性的主题时,不能依据个别事实建立或推翻理论假设,而要沿着时间线渐次考察,慢慢将它勾画清楚。孤立地抽取某个历史片段的研究方式是危险的,它能“轻松”地跨越数个世纪的各个层面的具体现实和整体背景,抽取特定的事件,而不顾及这种跨越可能带来的问题。古德森指出,使用了史实,并不等于开展了历史研究,必须对课程是如何形成的建立一种更为历时性的,“系统的演进式的理解”[42],而叙事正是展示时间上的延续性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古德森由“社会科学”研究启航,逐渐驶向历史的深处。而牵引着他,乃是结构与行动之间,抽象的群体概念与具象的个人生活之间,社会科学研究对“普遍性”的追求和历史的“特殊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当英美的课程社会学和批判课程理论普遍强调结构性的力量,强调“优势阶层对课程的控制”的时候,古德森通过细致的个例考察,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复杂性。他发现,在英国,基础教育中的地理科目,并不像根据理论推测的那样,由作为“优势群体”的大学地理学者对学术知识进行教学化改造而形成。恰恰相反,是通常被认为地位较低的中小学校教师推动了大学中地理学科的发展,是一个由下而上的推动过程[43]。
起初古德森倾向于从历史的实证经验中概括一些普遍性的模式,然而探究过程中,时常跳出来颠覆理论的“反常”令他越发尊重情境的特殊性,逐渐认识到特殊性本身便是历史的闪光之处。他开始书写教师生活史,去关注特定历史背景当中个人的体验和选择,因为这样做不仅揭示了机构和体制等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限制,也展现了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能动作用。古德森发现之前的课程研究在考察学校教育时“制造了一种流行的但却缺乏真实性的教师模式:教师个体基本上是可以相互换位的”,他们“千人一面”。难道无论是谁在当老师,也不管是在哪个年代当老师,课堂里的教学都会是同一个样子?显然并非如此。“古德森坚信教师不但在教学态度、教学技巧上有重要的区别,而且在对课程内容的认识、解释上,在课程编排和评估的行为模式上,也有源自其各自的生活史背景的重要区别……为了理解这些区别的重要性,必须将学校的研究重新与个人传记和历史背景的考察联系起来。”[44]以往的课程社会学研究没能展现行动主体本身的声音,而生活史研究则是首先尊重个人的“生活故事”,让人去讲述,去为他自己说话,而后再辅以社会历史的整体背景,构成一幅完整的画卷。“课程不仅意味着社会群体的活动,也意味着个体的经验。”[45]个体的经验、教育的经验的特殊性使得古德森选择了叙事这种呈现研究发现的新方式。
三、叙述学校情境中的经验
通过对上述三个个案的考察,我们尝试理解为什么叙事研究成为不同取向的课程研究者们的共同选择。三位学者,一个坚守在学校层面,传承和延续课程领域的核心工作;一个向内挖掘,关注个体的内在体验;一个向外拓展,审视社会力量对课程的塑造。施瓦布曾列出课程的四个基本要素(commonplaces/ desiderata),学生、教师、科目内容和环境。在这四个要素中,康纳利主要关注教师,派纳从学生出发,而古德森考察的是科目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理论取向和着眼点都不相同的课程研究者④,最终都走向了叙事研究,可见叙事研究在西方课程领域的兴盛绝不是一种偶然。
“如果有两个术语纠缠课程研究,那一定是‘理论’与‘实践’。”[46]课程学者们承受着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要面对两个不同的场域。在大学中想得到其他学科的学者们的尊重,就要对“纯粹”的理论建树孜孜以求;而走进中小学校时想不遭受冷遇,就得换上另一副面孔。随着课程开发活动的空间被压缩,课程领域似乎走到了一个分叉路口,“要么走向理论要么走向实践”[47],必须要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向当中选择其一。然而通过对学校情境中的经验进行叙事探究,研究者们有机会以新的方式将理论和实践相融通。
对课程叙事而言,课程就是“情境中的经验”[48]。有学者指出,关注学校情境中的经验乃是“课程领域代代相传的核心观念”[49]。课程领域曾一度出现脱离学校实践的理论研究倾向,这遭到了施瓦布的严厉批评。作为他的学生,康纳利也认为很多课程理论研究的失败之处在于忽视了学校情境中限制着课程实施效果的复杂因素,而叙事研究能发现并描绘这些因素。叙事研究的情境由实践情境所规定,面对的是真实的学校生活,研究不与实践脱节。古德森同样关注学校情境,他倡导研究者通过叙事打开学校这一“黑箱”,讲述里面的故事。有感于学校课程实践遭受的许多限制来源于学校之外,古德森曾一度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而通过叙事他完成了向学校的回归,返回来考察那些“结构性因素”对个人学校实践具体的作用方式。表面上看,派纳似乎不如康纳利和古德森重视实践,更强调理论的优先性。实际上他从根本上拒斥理论和实践二元对立的思维,认为理论生产本身便是实践,而“理论个人化就变成行动”[50]。他的“存在体验课程”则为各种借助叙事开展学习的课程提供了实践范例。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三位学者都是以理论化程度极高的方式从事着学术探究,但因为叙事,因为叙述学校情境中的经验,他们又都没有脱离实践。
叙事是“我们能够最接近经验的一种方式”[51]。课程叙事是直面学校鲜活经验的一种研究。通过“概念重建运动”,课程研究者广泛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精神分析等理论资源,这些来自欧洲的理论传统与课程研究诞生地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境的经验主义传统殊异其趣,将其他领域的思考方式移植到学校教育场域也会带来适应性不足和独立性丧失的问题。叙事能够帮助课程研究摆脱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避免成为其他学科的应用领域而“走向自主”[52]。康纳利、派纳和古德森等人在课程研究乃至整个教育学研究中引入叙事,显然是受到了其他学科的启发,但引入叙事,不意味着逃避教育学专门领域自身的方法和话语体系,而是逐步地形成了一种适合教育活动的理论方式。[53]三位学者都看到叙事研究在应对经验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方面的独特优势,都提倡用叙事去关照教育中的“人”和“事”。它帮助研究者向课程中的“人”回归,也向“事情本身”回归,不像课程研究中的“传统主义者”那样依赖僵化的旧有概念,也不像“概念-经验主义者”那样依赖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寻找新的方式处理理论概念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正是“概念重建”或者说“再概念化”的最终目的。派纳开启自传叙事时,他相信只有放弃当时课程研究中常见的“程序”、“技术”、“目标”和“评价”之类的词汇才能回到“人的教育经验”,展开叙事就是要消除理论语言与教育生活之间的区隔[54]。康纳利也把叙事当作弥合经验事实和研究工具之间的缝隙的黏合剂,因为叙事“既是现象也是方法”[55]。热心课程社会学研究的古德森则借助生活史叙事,成功地将自己对结构性问题的思考融入到对个人生活的考察中,由此切入到社会科学所应探讨的“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56]。
康纳利和派纳都一再地提及杜威对学校情境中的经验的研究给后人带来的启发。对杜威来说,研究教育“就是研究经验。”[57]他认为教育研究应该在自然的学校环境里而不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他不相信教育研究人员只是“心理学家和教育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中间人”[58],教育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然而在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一度是那些“除了收集数据以外不愿在中小学校里浪费时间”的人占了上风,尤其在课程领域里,行为主义心理学曾经大行其道,课程学者不得不扮演“中间人”的尴尬角色。幸好,这只是课程研究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已。拉格曼(Lagemann, E. C.)曾写道,“桑代克赢了,杜威输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就没有搞清楚教育研究的历史”[59]。从课程领域的演进状况来看,这个判断曾经很准确,不过要做结论的话,或许为时尚早。
注释:
。
② 泰勒的学生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③ 学生中就包括比派纳年长7岁的格鲁梅特和年长3岁的米勒,这两人日后都成了课程自传理论和女性主义课程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④ 这三位代表还来自不同国家,康纳利来自加拿大,派纳来自美国,古德森来自英国。
参考文献:
[1] [52] 张华. 走向课程理解:西方课程理论新进展[J]. 全球教育展望,2001,(7):40-48.
[2] [4] Schwab, J. J.The practical: A language for curriculum[J]. The School Review, 1969,78(1):1-23.
[3] [29] [38] 派纳,等. 理解课程:历史与当代课程话语研究导论[M].张华,等,译. 北京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86, 540-541,576.
[5] Herrick,V.,Tyler, R. Next ste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adequate curriculumtheory[A]. Herrick,V, & Tyler, R. Toward imptoved curriculum theory[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0: 118-124.
[6] Hlebowitsh,P.S.Amid behavioural and behaviouristic objectives: reappraising appraisals of theTyler Rationale[J].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992, 24(6): 533-547.
[7] Kliebard, H. M.The Tyler Rationale[J]. The School Review, 1970, 78(2): 259-272.
[8] Sears, J. T. J.T., Schubert, W. H.& Marshall, J. D. Turning points in curriculum : acontemporary American memoir[M]. Upper Saddle River, N.J.: Merrill, 2000: 52.
[9] Bruner, J.S. TheProcess of Education[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2.
[10] Tanner, D.&Tanner, L. N. Emancipation from Research: The Reconceptualist Prescription[J].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79, 8(6): 8-12.
[11] 王文智. 走向“后概念重建”的课程研究——以后结构女性主义课程史为例[J]. 全球教育展望,2014,(10):21-29.
[12] Connelly, M.F.Conceptual Disciplinary Structures and the Curriculum[R]. Report on Annualmeeting of the AER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February 6, 1969.
[13] [14] Connelly,M.F. The functions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J]. Interchange, 1972, 3(2-3):161-177.
[15] Connelly,M.F.& Dienes, B. The Teacher As Choice Maker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Case Study[R]. Report on Annual meeting of the AERA, New Orleans, February,1973.
[16] Connelly, M.F.Research Problems in Curriculums: Alternative Paradigms[R]. Report on Annualmeeting of the AERA, Chicago, April, 1974.
[17] [19] [20] [25] [28][46] [48]康纳利,克兰迪宁. 教师成为课程研究者:经验叙事[M]. 刘良华,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4,1,2,4,25,91,6.
[18] [21] Connelly, M. F., & Clandinin, J. D.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 at Bay Street School: Ritual, personal philosophyand image[A]. Halkes, R.& Olson, J. H. Teacher thinking: A new perspectiveon persisting problems in education[C]. Lisse: Swets & Zeitlinger,1984:134-148.
[22] [27] Clandinin,J.D. & Connelly, M.F. Rhythms in teaching: The narrative study of teachers'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 of classrooms[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1986, 2(4): 377-387.
[23] Clandinin, J. D.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 A study of teachers' classroom images[J].Curriculum Inquiry, 1985,15(4): 361-385.
[24] Connelly,M.F.& Clandinin,J.D. Teachers as curriculum planners: Narratives ofexperience[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8:31.
[26] [51] [57] 克兰迪宁,康纳利. 叙事探究:质的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M]. 张园,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196,xi.
[30] [31] [32] [33] [35][36] [54]威廉•派纳. 自传、:1972-1992课程理论论文集[M].陈雨亭,王红宇,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4,9,10,35,38,7.
[34] Pinar, W.F. TheMethod of “Currere”[R]. Report on Annual meeting of the AERA, Washington, D.C.,April, 1975.
[37] 丁钢. 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16-18.
[39] [43] Goodson, I.Becoming an Academic Subject: Patterns of Explanation and Evolution[J]. British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1, 2(2): 163-180.
[40] 迈克尔•阿普尔. 意识形态与课程[M]. 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5.
[41] Goodson, I.Subjects for study: aspects of a social history of curriculum[J]. Journal ofCurriculum Studies, 1983, 15(4): 391-408.
[42] [45] Goodson, I.The making of curriculum : collected essays[M]. London ; Washington: FalmerPress, 1995:184,59.
[44] 贺晓星. 课程研究的生活史视角[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83-88.
[47] [50]刘宇. 课程研究取向:历史演进与未来选择[J]. 全球教育展望,2009,(10):16-20.
[49] Hlebowitsh, P.S. Generational ideas in curriculum: A historical triangulation[J]. CurriculumInquiry, 2005, 35(1): 73-87.
[53] 丁钢. 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J]. 教育研究,2003,(2):22-27.
[55] Connelly, M. F.,Clandinin, J. D. Stories of Experience and Narrative Inquiry[J]. EducationalResearcher, 1990, 19(5):2-14.
[56]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像力[M].陈强,张永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54.
[58] 拉格曼. 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 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M].花海燕,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50.
[59] Lagemann, E. C.The Plural World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1989, 29(2):185-214.
Why Narrative Study in Curriculum: Based on Three Histories of Curriculum Academics
WANG Wenzh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Facing a highly differentiated curriculumfield, representative researchers in different campaigns (Connelly in “CurriculumDevelopment”, Pinar in “Phenomenology-Aesthetics” and Goodson in “Politics-Sociology”)all approached to narrative studies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standpoints anddifferent research questions. It is found in a review of their conversionjourneys to narrative that, narrative is a suitable way of theorizingcurriculum balanc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following theresearch tradition of dealing directly with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inschool contexts.
Key words: Curriculum studies; Educational Narrative;Curriculum History; Reconceptualization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右上角点击“查看公众号”可加关注
更多好文章,请查阅教育高等研究院网站http://www.iase.ec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