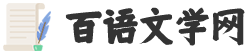文北师大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崔颖
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影视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安徽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参编《亚洲电影蓝皮书》系列丛书、《亚洲电影研究教程》《亚洲电影类型:历史与当下》等图书。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影视文化、少数民族电影。
民族想象、历史认同与印记:论新时期泰国电影的主体性建构
【摘要】新世纪以来,迅速崛起的泰国电影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亚洲电影的权力格局,成为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亚洲新兴区域电影之一。泰国电影的崛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其百余年电影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在历史创作经验的积淀下,新时期泰国电影面对新的市场和文化环境,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范式,完成了自身的主体性建构。这种基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主体性建构主要体现在泰国电影对民族身份的想象和认同、国家历史的记忆和叙述、宗教传统的书写和关照等方面。
【关键词】亚洲电影 泰国电影 主体性
在新世纪以来的世界电影版图中,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伊朗、泰国等区域电影异彩纷呈的发展格局无疑构成了蔚为壮观的亚洲电影多样性图景,“亚洲电影是世界上少有的,多元文化相互联系,又呈现必然差异、自足发展的状况,为世界电影提供了越来越明显的文化风貌。”[①]而作为亚洲电影的泰国电影,与印度、中国、韩国等电影大国之外的大多数亚洲区域电影一样,在好莱坞电影依然是市场主导并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霸权的背景下,在与好莱坞电影近身博弈和对话的过程中,试图确立自身特性并彰显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完成民族电影文化身份的主体性建构。
正如学者李道新将二十世纪的亚洲电影定义为一种“以国别相标识的、地理意义上”的“亚洲的电影”,而将新世纪的亚洲电影视为文化意义上的,“更具亚洲认同感和普世价值观、因而也更有精神包容性和市场竞争力”的“亚洲电影”[②]一样,新时期以来的泰国电影经过“新浪潮”运动的启蒙和洗礼,通过丰富多样且国际化的类型电影创作以及独树一帜的独立电影作者言说,无论从文化承载还是从市场竞争的维度进行考察,可以说都已实现了从“泰国的电影”到“泰国电影”的转变。而这种建立在本土电影主体性身份建构基础上的转变过程,主要体现在新时期泰国电影呈现出的对民族身份的想象和认同、国家历史的记忆和叙述、宗教传统的书写和关照等方面。
一、民族想象与自我认同
,“他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太大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③]对民族的想象意味着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是人类深层的心理建构。而电影是这种想象建构的重要叙事载体。于是,当查崔查勒姆•尧克尔在《素丽瑶泰》《纳瑞宣国王》等影片中将古时恢弘的暹罗宫殿和国王、王后的生活场景搬上大银幕,当朗斯·尼美必达在《鬼妻》中对十九世纪泰国乡村生活图景进行复原,当普拉奇亚·平克尧在《拳霸》中把当代泰国民俗和泰拳文化进行影像呈现,“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无疑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和演绎。而电影创作者和观众在创造和接受这些民族文化意象的过程中,共同完成了对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如萨义德所说的,“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构建的,有时甚至是凭空生造的。”[④]当然,对电影而言,这种人为的身份构建本身也是其艺术创作的主旨之一。
而在对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中,“他者”是不可或缺的。萨义德说过,“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⑤]在萨义德看来,每一时代和社会都会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对新时期的泰国电影来说,这一他者无疑是想象和发明了“东方”的西方。正是新时期泰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让西方世界“发现”了从属于东方文化体系的泰国电影,并对泰国电影进行西方视角的解读和阐释。而在与西方对话的过程中,泰国电影以独特民族文化特性,充满异域风情的影像风格,重塑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他者”语境中的主体性。正如英国学者瑞切尔·哈莉森在考察《鬼妻》时,认为影片通过对19世纪泰国乡村的准现实的描写,重现了泰国的历史文化。[⑥]哈莉森的这种对《鬼妻》的认知,本身就是对泰国电影主体性身份建构的认同。而泰国电影正是在这种与西方的对话中,完成了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
民族电影是身份想象和主体建构的载体,集结了集体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努力。在新时期泰国电影中,影片中的人物和故事也体现了这种集体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努力。在《拳霸》和《冬荫功》中,被盗的佛头和大象是泰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同时也是泰国民族身份的象征,为了找回佛头和大象,托尼·贾饰演的阿丁(《拳霸》)和阿锦(《冬荫功》)分别与曼谷的盗佛集团和澳大利亚的中国展开殊死搏斗。在这里,阿丁和阿锦是泰国传统文化的守卫者,同时也是民族身份的守护人。在“他者”的入侵导致民族文化遭到破坏和民族身份受到威胁时,他们挺身而出,捍卫族群的主体身份。最终,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洪来被杀,老象被做成标本),佛头被阿丁寻回,小象被带回阿锦的家乡。传统文化得以延续,民族身份也得到维护。相比之下,同样是自我身份的追寻者,爱情电影《二月》中的杀手基则没有那么幸运,混迹纽约的基一心想要回到泰国,无奈连机票都买不起,想要金盆洗手尽快回家的他遇到了娇坦,一系列变故之后,基客死他乡。影片中,身处异乡的基其实也是在努力追寻自我身份的认同,不过,在他看来,只有回到家乡的空间,才能完成这种认同。可惜,他的这种努力失败了。在这里,电影的人物和空间转化成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样本,承载了对身份的想象和对主体意识的建构。
二、历史重述与民族叙事
在文化和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西方为中心视角的好莱坞电影开始对亚洲的历史进行重写,并输出到各国的电影市场。如关于中国历史的《末代皇帝》,关于越南历史的《印度》以及关于泰国历史的《安娜与国王》。这些影片大多是西方对东方历史想象的影像书写,呈现出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进行的电影创作在被书写的民族国家看来,无疑是扭曲的,充满了殖民情结的偏见,因此,也必然遭到相关国家的反感和不满。如1999年上映的《安娜与国王》,因其对泰国国王生活的描写被泰国王室认为扭曲了历史事实,损害了国王的形象,是对泰国王室的不恭而被禁止在泰国上映。
而作为对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抵抗,亚洲电影也开始以现代化的影像语言重新书写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挖掘被西方话语体系误读和扭曲的历史事实。于是,关于本民族的历史记忆通过民族化的叙事风格在一系列电影中呈现出来,重构了本国观众关于历史和文化的想象,完成了对西方殖民话语的反击。
在新时期的泰国电影中,涌现出不少这种重返历史现场,重置历史情境和重构历史经验的影片,比如《素丽瑶泰》《烈血暹罗》《大将军》《大城武士》《琅卡苏卡女王》《纳瑞宣国王》等。这些史诗影片大多由泰国王室资助并参与拍摄,如《素丽瑶泰》和《纳瑞宣国王》(1至6部)的导演查崔查勒姆•尧克尔就是泰国王室的一名王子。在王室的支持下,《素丽瑶泰》动用了多达2000人的群众演员和80头大象参加拍摄。在特效制作上则不惜重金与好莱坞的特效公司进行合作。这种重金打造的视听奇观影片带给观众的冲击力和震撼效果丝毫不亚于好莱坞高概念大片。这些在电影市场创造票房奇迹的影片用西方先进的表现技巧,结合民族化的历史叙事,重塑了被西方殖民史观主导下的好莱坞电影所扭曲的历史,完成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建构。
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有所不同的是,泰国电影在追溯民族历史时,大多强调的是国王、王后等英雄人物的史诗书写,而较少突出普通个体或群体的抗争。这与泰国绵延近千年而未曾中断的的王室传统有关,也与其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未被殖民过的历史身份有一定关联。如《素丽瑶泰》的主人公素丽瑶泰就是泰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她一生爱国爱民,年仅35岁就战死沙场,为国捐躯。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庞大,创造了近4000万美元票房的《纳瑞宣国王》(1至6部)则是关于泰国“五大帝王”之一的、泰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大成王朝国君纳瑞宣国王的故事。
可以说,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与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力量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新时期泰国史诗电影将历史重述与民族叙事相结合,建构了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情感,提出了对本国民族文化复兴与价值重构的理解与思考,完成了民族历史身份的重建和认同。
三、印记与女性关照
在90%以上的国民信仰的泰国,文化对电影的影响无法回避。对泰国人而言,“已深深地渗入到泰国人的心理和民族性格之中,成为泰国人判断是否和衡量伦理道德的准则,成为泰国人的精神寄托。”[⑦] 同样,对于精神世界外化形态的电影来说,给予了泰国电影丰富的精神滋养,而电影也成为传统的重要文化载体。正是这种独特的传统印记,使泰国电影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气质,成为泰国电影独特性的意象所在。
泰国电影中的印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对小乘中“业报轮回”观念的诠释和演绎。 “业报轮回”是观念中最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学说,用通俗的话语概况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在泰国电影尤其是恐怖片的电影创作中,“因果相续,报应不爽”一直是影片的内在叙事逻辑。[⑧]比如,《鬼影》中的娜塔因爱生恨的复仇,《恶魔的艺术:邪降》中看似无辜的青年男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的惨痛代价,《三更之轮回》中的唐师傅因贪婪而召来杀身之祸。这些影片中,“轮回”和“报应”成为叙事的重要符码,也是理解影片内在涵义的关键路径。特别是在《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这样的作者电影中,意象成为最重要的叙事要素,观众如果对“前世”、“今生”、“死亡”、“新生”等观念缺乏基本的认知,就无法理解影片表达的深刻内涵。
与历史上的泰国电影相比,新时期泰国电影的文化阐释加入了东方式的哲学思考,使得影片呈现出西方视角下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猎奇式的关注和“凝视”。而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在通过生动的影像表达满足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的同时,也完成了泰国电影自我文化价值的建构,这也是新时期泰国电影对其历史形态实现的一种超越。
对女性的关照同样也是新时期泰国电影的独特性所在。在劳拉·墨维(Laura Mulvey)看来,电影中的女性是作为“男性凝视”的对象而存在的,“在传统上,作为被展示对象的女性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她既是电影故事中人物的色欲对象,又是观众席中人物的色欲对象。”[⑨]劳拉·墨维提出这一论断已过去四十余年,虽然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女性地位已有极大提升,但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电影中所建构的虚拟社会中,男性无疑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在大多数电影中,女性仍然处于被男性“凝视”和消费的从属地位。不过,在泰国电影中,女性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极大改变。在新时期泰国恐怖片中,以“鬼”的形象出现的女性往往作为受害者对作为加害者的男性展开报复,比如《鬼妻》中的娜娜对村民的戕害,《鬼影》中的娜塔对者的复仇,《厉鬼将映》中扶桑嫂对冷血剧组的杀戮等等。在这些恐怖电影中,“女鬼”通过超能力对男性展开复仇,对男性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而在《女拳霸》《怒火凤凰》等动作片中,女主角雪和迪尔则直接用拳脚瓦解了压迫她们的男性世界。
泰国电影中女性角色对男性世界的挑战和瓦解,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传统东方伦理价值观念的一种颠覆与解构,而似乎只有在泰国这个既有保守的宗教传统,又有开放多元的世俗文化的国度,这种颠覆与解构才能成为可能,尤其是近年来包括《想爱就爱》等影片在内的大量LGBT[⑩]题材电影的出现,让泰国成为酷儿群体心目中乌托邦式的理想之地。而新时期的泰国电影至少在女性身份的建构上,或许已经完成了其他亚洲电影尚未完成的或无法完成的使命。
四、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亚洲电影的泰国电影,在新世纪以来亚洲电影多样性的发展图景中,在好莱坞电影依然占据世界电影市场主导地位并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霸权的时代背景下,新时期泰国电影以独特的民族文化特性,极具地域风情的影像书写,以及丰富多元的类型化创作,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并在与好莱坞电影的博弈过程中确立了本土电影的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创造出风格独具的电影范式,并通过对民族身份的想象和认同、国家历史的记忆和叙述、宗教传统的书写和关照完成了自身主体性建构,成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伊朗之后又一代表性的亚洲电影新力量。
[①] 周星,张燕.亚洲电影蓝皮书2015[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2.
[②] 李道新. 从“亚洲的电影”到“亚洲电影”[J].文艺研究,2009,(3):78.
[③]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④]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27.
[⑤]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26.
[⑥] Harrison ,Rachel.(2005).Amazing Thai film: The rise and rise of contemporary Thai cinema on the international screen. Asian Affairs,Volume 36, Issue 3:327.
[⑦] 姜永仁,傅增有.东南亚宗教与社会[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210.
[⑧] 赵轩. 从《鬼妻》到《鬼夫》:泰国恐怖片转型及其文化意义[J].东南亚研究,2014(4):102.
[⑨] [英]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9.
[⑩] LGBT是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
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