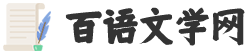B言B语:2018年4月12日,微信公众平台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大抵意思是我在N年N月注册过一个公众号,如果在4月24日之前没有登录的话,它将会把此号报销。我想:嗨,何不运用起来,发点儿我写的小说呢!于是乎,我决定就这样干了。接下来,我的公众号里,将不定时发送我的长篇小说——《时光餐厅》。各位无聊了可以看看,如果有急事要忙,不看也没什么损失。
时光餐厅
一
这一天和人类的任何一天并无不同。
我和拖把是怎么认识的,我忘了。说起来真是奇怪,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仿佛某一天,她像喷泉一样就冒了出来,然后站在我的面前,带着她一贯的天真和不屑,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吧,我们去喝一杯。于是,她就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有些事情你完全解释不清楚,就比如我对她的情感,我总是觉得,拖把,这个雌性动物,和我这头雄性动物,天生就是在一起的,作为我的一部分存在着。只是在不相识的那段空白岁月里,她去某个遥远的小镇买一个特制蛋卷,而我,就站在时间的候车室等她。我度过了那段混沌的岁月,然后她和她的蛋卷同时出现了,她跳过来,在人群中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吧,我们去喝一杯。于是,我就出现在了她的生活里。
有时候我想,她一定是上帝从我肋骨上取下的那根骨头吧。
不管怎样,我和拖把,就像老鼠与老鼠贴紧紧地沾在一起,很难分开了。当然,要是拖把看到了这个比喻,一定要跳起来追着我打,她最讨厌老鼠,和老鼠有关联的一切事物都是她不能容忍的,比如鼠标。她会说,哎呀,这样子好讨厌!这都什么时代了,还用这么low的东西,你们人类真是落后啊!
有一次,我们去九芝堂书吧,在街上看到一个卖烤红薯的,她露出一副极其嫌恶的表情,说,这种东西只有你们人类才吃得下吧!我说这是粮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就站在路口,叉着双手,说,可是这样子很恶心啦!我走到烤红薯摊跟前,转过身对她说,你想吃大个的还是小个的?她咦了一声,拔腿就跑,转眼间不知所踪。
在生活中,拖把从来不隐藏情绪。她的好恶悲喜,全从她那双大得离奇的眼睛里流露出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被她吸引的原因。
时间是公元2048年,地点是地球的某座城市,这座城市有一个怪好听的名字:斑马纹。但通常我们都不叫它斑马纹,我们叫它city of hope ,有时候为了方便,我们直接叫它“希望”。“希望”是一个消极的词,通常情况下,人只有在极度绝望时才会祈求希望,只有在这个语境下,希望才有了它的现实意义。“希望”一旦得到确立,它就显得空洞、虚伪、滑稽和矫揉造作。
公元2048年,我和拖把住在地球上一座名叫“希望”的城市里感受着绝望。当然,绝望也仅仅是我的看法,我不知道拖把怎么想。我问过她,你住在这里绝望吗?她白了我一眼,说,我为什么要绝望?然后她穿上她的驼色大衣,踩着她的红色高跟鞋出门去了。出门之前,她转过身看着我,说,漂亮吗?我说,挺漂亮的。她给我一颗飞吻,消失在了门口。走廊上飘来高跟鞋的声音和愉快的口哨声——这时候我才想到,拖把,这只雌性,对人类的绝望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所以那段话应该改成:
公元2048年,我住在地球上一座名叫“希望”的城市里独自感受着绝望。
拖把每天都要去“上班”,其实她的上班称之为“游荡”更为合适。任务在我们眼里看起来就像一顿美食。她每天都去大街上逛,用她手腕上那个像手表的装置收集图像和声音,然后回家,将采集到的这些素材,上传到一个黑盒子里,然后再由这个黑盒子转换成一些奇奇怪怪的代码发射到宇宙中的某个角落。她把这个行为称为“人类调查报告”。我说你为什么要搞这个“报告”?她反问我,你没有写过毕业论文吗?我说你这么说意思是你还没有毕业?她想了一下,说,可以这么说。我说那你这是本科呢还是专科?她说什么是本科什么是专科?我不得不给她普及了下什么是本科什么是专科。听完之后她说,这是你们人类独有的分法吧?!怪不得你们发展得那么缓慢,连教育也要分等级的啊!我说这不是分等级。她说你说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她说教育是平等的,知识是共享的,你们把它分配得太糟糕了。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更深的见解。我说,那怎么可能实现嘛!她说,这就是你们人类的缺陷了!在我们RWAWU,这很容易实现,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有吸纳功能,也就是说,每项新的研究成果一旦确立,我们就能马上接收到信号,并且有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说,好吧,这种生理性的缺陷真是不能对比的。她说,其实也不是生而有之,这是一项技术,只是和我们的身体已经结合得相当完美了而已。像我们祖先,那些早期的RWAWU居民,在没有这项技术之前,还不是和你们人类一样愚蠢。拖把用了“愚蠢”一词,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愤怒,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如果人类不愚蠢,那就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形容这个物种了。
她也知道,这个词从感情角度来说,是会让人伤心的。她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人是会达到更高级别的。我说其实我并不关心这些,我只是想到我的小说进行不下去,有点儿沮丧而已。她说,给我看看。我把稿子递给她。她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边看起我的小说来。
源从巷子口转进来,朝前走了35步,然后左转身,拿出门禁卡,哔的一声,铁门打开了。源走进昏暗的楼道,登上三级台阶,来到门牌号是2127的房间门口,插进钥匙,旋转,打开门,走进去。镜头就在那扇门关闭的瞬间结束了。
源每天都会重复相同的动作,有时候是去外面吃个炒面,有时候是去买两包烟,有时候,仅仅是去大街上走走,回到巷子口,一切又像电影里安排好的镜头。他不需要付出什么,为了这个镜头,仅仅是完成,然而效果是相当的完美。
源是个杀手。
源住在斑马纹东街,东街是一条平民街,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源就住在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很有隐蔽性,因为什么人都有,所以人待在那里不会觉得突兀。但源住在东街,并不是为了隐藏自己,他不需要隐藏什么,即便他是个杀手,他也不需要隐藏什么。更何况,除了死在他刀下的那些人,谁又能在大街上辨别谁是杀手呢?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杀手。所以他不需要隐藏什么。
源住在东街,是因为他能住的只有东街,没有什么地方比东街更适合杀手居住了。
源住在东街一座叫冷水台的旅馆里——这里的旅馆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像什么犀牛角啊翡翠居啊月亮岩啊,而源,住在冷水台。如果把一栋旅馆比作是一个生物体的话,那源就是寄居在这个生物体里的细菌。“细菌”是一个浪漫的词。它细微却又无所不在。它主宰却丧失权利。它庞大却非肉眼所能及。所以它显得神秘,吊诡,璀璨,虚无。它是美和邪恶的综合体,一如杀手这个词。
源每天待在他的房间里。睡觉,起床,吃两片镇定剂,有氧运动,打开电视机,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书。他每天都做着相同的事。他喜欢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也是我——作者——给他的定义,其实至于他喜不喜欢,我还真不知道,我们暂且将就这个说法吧。
源在等一个人。
源住在冷水台2127号房。
源在等一个人。
拖把说,没了?
我说,这就是我感到沮丧的原因。
拖把放下稿子,摇摇我的肩膀,说,没事,慢慢写吧,我养你呢!哈哈。
我没有说话,我感到有些伤感。
拖把说,去洗洗脑袋吧,油死了!
我起身,去厕所。我把水温调好,洗发膏抹在头上,忽然间我又不想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