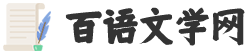作为问题的“问题意识”
从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命题缺失现象切入
作者:尤陈俊,法学博士,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基础法学教研中心副主任、《法学家》杂志副主编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本文已获得作者和刊物的授权,刊出时稍有删减并去掉了注释,引用请以纸版为准。
【内容摘要】
那种按照教科书式体例撰写的法学论文,其最大的弊病在于“有论域而无论题”,亦即只是选定了一个研究领域、对象或范围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和叙述,却没有从中提炼出一个中心论题贯穿全文始终并加以论证。这种教科书式的写作风格,在今天仍然顽强乃至顽固地继续影响着法学论文的写作,在很多题为“××制度研究”或“论××制度”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当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之所以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与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和认识误区有关,特别是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Question)、话题(Problem)和命题(Issue)之间的区别。对于如何提炼问题意识这一问题的思考,可以围绕“书本知识VS. 社会实践”、“历史视野VS. 现实关怀”和“意识VS. 国际视野”这三组概念展开。
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尤其是1999年开始的全国大学扩展以后),的法学教育和法学作品生产均在规模上总体呈现出快速发展甚至急剧膨胀的趋势。但在这种“繁荣”景象之下,却时常可以听到很多叹息之声。一方面,每年的春季学期,常常会有很多法学教师抱怨阅读一些无甚学术新意的毕业论文并撰写评阅意见实在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折磨。另一方面,在国内各法律院系硕博士研究生每年通过答辩的两三万篇毕业论文和各种刊物上每年发表的成千上万篇法学论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论文实际上很少受到同行们的关注,甚至有个别论文在收录于知网数据库并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后,还出现了“引用量为 0、下载量也为 0 的现象”(这意味着连作者本人都懒得把自己的文章下载来看或加以保存)。
那些让评阅老师们“怒其不争”或为同行们所无视的所谓法学论文,之所以有如此命运,主要是与其学术质量不高乃至低下有关。而在导致其学术质量不高乃至低下的各种原因当中,除了有一些法学论文可能存在胡乱抄袭拼凑的学术不端外,很多法学论文本身缺乏“问题意识”是一个常见的共同点。因此,本文将以当代法学论文写作为论域,将“问题意识”进行问题化处理之后,再渐次展开讨论。
一、“有论域而无论题”的通病
在各校的法学研究生们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当中,有一类模式的论文题目相当常见,那就是“××制度研究”或“论××制度”。一些部门法研究领域,更是此类单调的模式化论文题目的重灾区。在我看来,此类题目不仅因几乎千篇一律而欠缺文字表述方面的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正文内容很多都缺乏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论题(更加不用说论题在学术上的创新性),而只是将与某种法律制度或法律现象有关的方方面面知识点都加以介绍、梳理和叙述,亦即“大都是按照题目对相关方面所做的‘知识性’的描述,而根本不是以某个理论问题而勾连起来的思考”。 用一位学者的俏皮话来说,“结果,别人写议论文,他写成说明文了!”
稍稍翻阅这些作品,便不难发现这些论文当中有很多都属于“有知识(介绍)而无(个人)见识”,在写作框架上几乎与教科书无异,以至于题目是“××制度研究”或“论××制度”,但其内容实际上变成了“××制度说明”或“××制度介绍”。在我看来,这种按照教科书式体例写就的论文,其最大的弊病在于“有论域而无论题”,亦即只是选定了一个研究领域、对象或范围,却没有从中提炼出一个贯穿全文始终的论题并围绕其加以论述。例如,一篇题为“私募股权投资中的对赌协议研究”的法学硕士学位论文,其行文结构是“对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的相关概念、本质、价值、运作机制及适用中的法律障碍等问题做一个分析”, 就属于上述所说的这种情况。在知网中所收录的各校法学专业硕博士学位论文当中,存在此种情况的论文相当常见。
二、问题(Question)、话题(Problem)和命题(Issue)的联系和区别
这种教科书式写作体例之所以在当下的法学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中仍然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是与长期以来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和认识误区有关。在我看来,这种认识误区的表现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其一,误将“选题”实际上等同于问题意识;其二,误将教科书以及一些著作所体现的“体系意识”实际上等同于“问题意识”。
多年前,一位曾在耶鲁法学院求学的学者曾专门撰文介绍道,“法学博士论文应该有‘命题’在西方是一项普遍性的要求”,“它应该是贯穿整个博士论文的中心论点,是你试图在论文中探讨或论证的一个基本问题(general issue)或基本观点(general position)”,且一篇论文的中心命题只能是一个,并强调说,“论文的命题即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研究的终结点”。 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在学术训练中这种对“命题”之不可或缺性的强调,与其建立在对Question、Problem和Issue这三个概念加以区分之基础的“问题意识”的极度重视有关。Question、Problem和Issue这三个英语单词,虽然看起来似乎都可译为“问题”,但其实存在着微妙的差别。仔细琢磨其各自的内涵,可将Question译为“问题”,将Problem译为“话题”,而将Issue译为“命题”或者“论题”。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中,这种须从拟解答的问题中提炼出一以贯之的中心论题(Issue)并围绕其展开论证的要求,并非仅适用于学位论文(dissertation)的撰写,而几乎是所有学术刊物对论文(article)所设定的固定格式。
法学院的很多教师在指导学生撰写论文时,通常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选题”方面。不少法学教师对学生如何选题的指导,实际上还只是停留在问题(Question)或话题(Problem)的层面,基本上都是从应当如何确定论文题目的大小(通常都青睐“小题大做”)、论文题目中所应有的主要知识点在写作提纲中有无大的遗漏等方面着眼,而往往未能提升至命题(Issue)的层面对学生加以训练。例如,一位前辈学者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谈如何撰写民法论文的文章,其中以撰写法人制度的论文作为例子谈论文定题,并根据所涉问题的大小,分级列举了一些论文题目作为参考,亦即“一级,如论法人制度的历史发展、论我国法人制度等;二级,如论企业法人制度、论财团法人制度等;三级,如企业法人成立的条件、企业法人民事责任的承担等;四级,如论企业法人章程、企业法人工作人员的民事责任等”。 另一位前辈学者出版了一本讲法学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册子,在学生当中很受欢迎。该书专列了一章谈学位论文的选题,其中列举了一些其认为较好的博士论文题目设计,均是“××问题研究”之类的题目。 上述这两位学者都是我非常景仰的前辈,但坦率地说,就他们所推举的那些论文题目而言,其实只是道出了拟研究的问题(Question)或话题(Problem),或者说只是提示了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此类题目的论文,虽然不排除其正文当中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命题(Issue)的可能性,但往往有更大的可能性是全篇以教科书式的体例面面俱到地铺陈展开,亦即实际上是基于教科书所注重的“体系意识”而非论文更应注重的“问题意识”进行写作。
这种“有论域而无(贯穿全文的)论题”的写作风格,并非仅见于一些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在一些所谓学术专著当中亦时可看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很多学术专著不过是主题较窄的教科书”。 不少此类题目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学术专著,虽然大致存在知识体系完备性方面的差别,但通常均缺乏一个贯穿全文的命题。这种现象,在我看来,与上述那种主要是注重如何划定研究对象或范围的选题习惯之内在缺陷所造成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而那种选题习惯之所以仍然顽强乃至顽固地延续至今,又与改革开放以降的前几十年里(这是法学恢复和重建的时期)法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教科书法学”的写作风格流行——烙在此时期成长起来的很多研究者身上的思维印记有关:“教科书通过教学,培育了未来的教师和学者,也因此既奠定了这些潜在的法学作者的思想图式,也灌输了其写作方式。”
一些更年轻的法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上述弊端,转而强调法学研究应当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就法学论文写作而言,最关键的在于如何发现、提炼和论证一个有学术创新性的命题(Issue),而并非只是划定了一片大致的研究范围进行缺乏中心命题的体系化叙述。陈瑞华举过一些貌似面面俱到但缺乏问题意识的“教科书式写作体例”的论文作为反面例子,“比如一篇有关民事侵权问题的博士论文,体例上包括侵权的概念、历史发展、、有关发展动向、侵权法的问题和侵权立法的现状、未来侵权法立法的若干设想等部分”。 何海波也指出,一些学生仿照教科书中某章某节的标题拟定自己论文的题目(例如“论缔约过失”、“行政检查研究”),却没有意识到在实践中或理论上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以至于写出来的文章“既没有重点也没有结论,既不要坚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既不和人家商榷也没准备被人家质疑”。 对于何海波所批评的这种写法,姚建宗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由于不少研究者错误地“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或研究‘范围’当做自己所研究的‘问题’”。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法学研究者在自己写作时注重对问题(Question)、话题(Problem)和命题(Issue)的区分,意识到问题意识对于一篇论文的重要性。举我自己几年前撰写的一篇小文章为例。我的那篇文章,从几乎任何一本《法制史》教材均会提及的“秦代是以身高来作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入手,对“秦代为何是是身高而非年龄作为刑事责任能力之分类标准”这一问题(Question)加以追问,通过考察秦汉时期国家认证能力的变化这一话题(Problem),最终证立了一个命题(Issue),亦即认为秦代论处刑责时以身高为准而汉代以来则改以年龄而断这种发生在刑事法制领域内的变化,是从先秦至秦汉时期国家在“基础性权力”方面得到提升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青年法学教师在指导学生撰写论文时,也更加注重引导学生们首先须基于问题意识提炼出一个命题(Issue),而不是让其选定了一个问题(Question)之后便开始方方面面铺陈开来写作。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是,之前相当常见的那种“××制度研究”或“论××制度”的学位论文选题,如今在很多法学青年教师那里已很难获得通过,故而此类题目的论文数量也相对有所减少。
三、问题意识从哪里来?
真正的问题意识,乃是建立在对问题(Question)、话题(Problem)和命题(Issue)之联系和区别有明确意识的基础之上。所谓“问题意识”,用一位学者所做的精炼概括来说,是指“作者必须发现现实中存在的问题(question),从中提炼出一个学术上的话题(problem),然后给出自己的命题(thesis)并加以论证。” 那么,这种问题意识具体可以从何处提炼?
(一)书本知识VS. 社会实践
在我看来,问题意识既可以是来自对书本当中的某一知识谱系的梳理、总结和反思,也可以是来自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一些现实困惑所带来的智识触动。
前述提及的那篇拙文,通过分析秦代在论处刑责时以身高为准而汉代以来则改以年龄而断这种变化的背后原因,揭示了其所反映的乃是从先秦至秦汉时期国家在认证能力上有着一个重大的飞跃,这种问题意识便主要是来自阅读相关历史文献后结合相关理论的思考。此类主要由对某一知识谱系重加审视而生发出来的问题意识,多见于法学研究中一些重思辨或偏考证的领域,例如法哲学、法制史、法律思想史以及法学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常常体现为一种书斋中的学问(或者借用顾培东的一个概括来说,主要是一种“知识-文化法学”的研究 )。
与之相对,另一类问题意识则主要来自社会实践中(亲身体验或调研所得)所接触到的一些现象所带来的触动与刺激。例如陈柏峰的一篇研究基层社会的弹性执法(此即“话题[Problem]”)的论文,其问题意识便是源于他在2007年4月至2014年7月间在湖北省某市多次对禁止非法机动三轮车(当地称作“麻木”)的执法情况进行调研时所发现的执法不严现象(此即“问题[Question]”),通过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弹性执法发生在法治的特定实践中,有着转型期独特的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背景,即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利益矛盾、尚难容纳多元利益诉求的法律系统、执法对象激发的社会话语压力、青睐变通权宜的法律文化四者之间的张力与合力”这一命题(Issue),并进一步将之提升至执法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之关联的理论高度予以延伸阐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第二类问题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借助于相关学术理论的印照,不然往往便会沦为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和展示(就像一些调查报告那样),而无法从“问题(Question)”中提炼出具有学术意义的“命题(Issue)”。例如,苏力从一起拼凑但不是虚假的“私了”案件入手,讨论了“法律规避”这一理论性话题,并进而论证了“法律规避是制度创新的一种途径”这一富有学术冲击力(同时也具有学术争议性)的命题; 这种讨论深度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他对于西方学术界的法律多元理论的知识储备和熟练运用。只不过相对于那种主要由对某一知识谱系重加审视而生发出来的问题意识而言,此类问题意识首先是由社会实践而非书斋中的单纯玄思所激发。这种情况,在那些立基于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的法社会学研究论著中相当常见。
有学者将论文的选题分为理论性的选题和实践性的选题两大类。 在我看来,即便是实践性的选题或应用型的法学论文,也应当有一个贯穿全文的“命题[Issue]”,而不能写成面面俱到的法律实务操作指南。只不过相对于理论性的选题而言,实践性的选题中的那个“命题[Issue]”,在理论深度方面的要求可以稍低一些而已。
(二)历史视野VS. 现实关怀
一些学者认为,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强调应当以当下存在的真实问题为研究对象。这种对问题意识的理解,在我看来有些失之片面。这是因为,第一,如上所述,确定了研究对象,并不等于就确立了“命题(Issue)”;第二,有学术价值的“命题(Issue)”,未必全部皆是来自当下现实问题的刺激,基于对历史的思考,也能开掘出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命题(Issue)”;第三,一些基于对某个反事实假设(Counterfactual hypothesis)的研究而得出的“命题(Issue)”,也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
从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实践当中提炼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意识的例子,兹举两例。支振锋通过对清末以来社会变革中为何法治并非主导话语这一“问题(Question)”的考察,对法治与国家能力之关系这一话题(Problem)进行探讨,最终证立了如下“命题(Issue)”——强大的政府(主要体现于国家能力方面)对法治而言是一种威胁,但它同时却又是所谓后发国家法治建成的前提。 基于类似的思路,另一位学者以近代探寻宪制的实践为何困难重重作为“问题(Question)”,,,,并从传统社会形态和现代化特殊路径的角度对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进一步加以解释。
基于某种反事实假设(Counterfactual hypothesis)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对其加以研究后证明了一个“命题(Issue)”,这种研究方法的首创者为美国的经济史学家、199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在他那篇1962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中,罗伯特·福格尔首先提出了一个反事实问题(亦即如果美国直到1890年还没有铁路,那么其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通过研究,他认为这最多影响到1890年美国国民收入的5%,亦即对于当时美国的经济而言,铁路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并没有通常所想像的那么重要和不可或缺。 尽管福格尔的这种反事实(亦有人将之称作“反设事实”)分析方法也受到一些非议,但不可否认,其能够帮助我们极大地丰富对历史现象和问题的认识, 故而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学术影响力,为一些研究者所效仿。例如,剑桥大学教授埃文斯(Richard J. Evans)便采用这种方法,出版了一本分析诸如“假如英国并未参与‘一战’,那么……”之类反事实历史的著作。 当然,法学研究中采用这种反事实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出色作品,迄今还非常罕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这种方法论证某个“命题(Issue)”的作法就完全与法学研究无缘。举一个例子来说,针对“假如‘依法治国’没有在1999年被写入我国宪法,那么……”这一反事实问题的细致研究,可能比那些泛泛地谈论1999年我国时“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的意义的文章要更有学术启发性。
(三)意识VS. 国际视野
近年来,国内的很多法学期刊都开始明确声明,其遴选文章的主要标准之一是看稿件有无“问题意识”,倡导学者的法学研究应当立足于问题。影响所及,纯粹研究外国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和法律历史的论文,如今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在国内的法学刊物(尤其是好的法学刊物)上发表。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新时期对法学之学术主体性意识的重申和强调。
自晚清变法以来,的法制与法学深受西方的影响,以至在“主体性意识”方面常常有所缺失。这种情况也曾引发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反醒。就法制方面而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民国时期阮毅成所指出的那种“‘看不见’的法律”现象:“在别的国家,人民只服从本国一国的法律;而在我国现在,因法律乃凑合各国法律而成,人民几有须同时遵守德、瑞、暹、土等许多国家法律的现象。” 就法学方面而言,其典型体现之一便是民国时期蔡枢衡的如下这番忧思:“今日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出身法国者,必对Duguit之学说服膺拳拳;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 在今天的法制与法学当中,这种情况仍有所见。顾培东曾对当下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类似现象作过形象的刻画,批评很多法学论文“讨论的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引证的是西方国家的立法制度,甚至援用的案例也是域外发生的事件。阅读这些论文,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这些论文是否出自法学人之手,论文的作者是否真的把读者作为自己言说的对象。” 陈瑞华曾举过一篇关于法律论证理论的中文论文作为具体例子,指出该论文“使用了德国的案例或者教科书上所使用的例子,引用了德国教科书上的图表,论证了德国法上的概念,试图与德国的法律论证理论论域的学者进行对话,但是却使用了中文在的刊物上进行发表”。 套用苏力的话来说,这些中文论文的作者其实缺乏一种面向学者写作和交流的“读者/受众感”。 就此而言,国内越来越多主流的法学刊物在选稿时日益重视“问题意识”,通过这种选文方面的导向性,有助于改善法学知识生产的学术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一篇论文号称其所研究的是问题,便等于就具有了问题意识。事实上,有不少看似研究问题的法学论文,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虚假或伪装的“问题意识”,亦即实际上把外国的法学理论和制度视同于公理、定理、定律,而只是将问题当作其下的“例题”加以验证和分析而已。张广兴描述了这种情况的几种具体情形,例如“忽视问题的特殊性,把的问题与外国的问题同质化,把用来解决外国问题的理论和制度作为理论根据和设计标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陈瑞华将这种思维模式形象地概括为是“把西方国家的共同理论和趋势当作逻辑的大前提,问题当做小前提,结论就是应该遵循西方的法治发展路径”,并将之斥为犯了方法上的幼稚病。 顾培东也批评过一些法学著述的此类套路——“在一些著述中常常潜含着这样的逻辑:西方国家存在的制度,就应当有;反之,西方国家没有的制度,也不应有。对于共有的制度,西方国家是此种性状,就不应是彼种性状,否则就是‘不规范’或‘不完善’。” 田雷认为这种套路体现了“找寻西方之良药来救治之顽疾的学徒心态”,并对“这种套路在法学院内的统治力”颇多感慨。
上述那种虚假的“问题意识”,未必皆是作者本人刻意的伪装,有时可能是根源于其所熟悉并惯用的外国法学理论对其思维方式的潜移默化影响,易言之,源于思维方式方面对外国法学理论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习焉不查。任何一套外国的法学理论(哪怕是其关于法的研究理论),均有其特定的生成背景,皆是基于特定的问题意识而被创造出来,因此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进一步来说,西方法学理论对我们的影响,并不仅仅只是提供了某种分析框架和解读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还会实际上宰制我们提问的方式和角度,亦即具有一种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议题设置同构化的潜在效应,进而可能使得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成为西方法学问题意识之下的衍生物和附属品。
一位教授宪法的青年学者曾反思道,“就当代而言,美国宪法虽然无法用于的宪法实践,但是极大地左右了人的宪法思考”, 以至于的一些学人在思考宪法和宪制问题时,几乎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被其当作“神话”的美国宪法、宪制及其相关理论,从而实际上顺着“在哪些方面美国有而无,因此也应该在这些方面补上”的思路往下思考。这种思路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美国神话在的泛滥不仅撕裂了学界的共识,也破坏着宪法文化的建构过程。” 借用络德睦(Teemu Ruskola)的一个洞见来说,这实际上体现了历史中形成的那套区分创制了法律主体与非法律主体的法律东方主义话语所造就的阴影——“美国人构成了法律的主体,而人则构成了无法律的非主体” ——在当代的某种遗留和延展。
还有一些学者以某法律制度、实践或问题在国外属于前沿话题但在我国还未能被作为一个话题加以研究或对其研究不多为理由,认为这体现了我国和国外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巨大差距,亟需奋起直追,于是热衷于撰写发表诸如“×国的××制度及其对的启示”之类的文章。但是,这种情况所反映的未必皆是差距,也有可能是差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上述那种庸俗的“问题意识”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将原本价值多元的差异直接转化为有价值位阶之落差的差距”。 例如,美国的很多法理学家和宪法学家都热衷于讨论堕胎自主权、安乐死、同性恋、、枪支持有、吸食大麻等话题,并围绕这些话题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有学术份量的论著(德沃金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对于来说,这些话题均大多数并不具有其在美国法学研究当中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性,至少不是当代最迫切需要法学研究者予以关注的话题。顾培东对上述那种所谓的问题意识进行过批评:“一些法学人热衷于关注域外的理论问题,以参与世界法文化讨论的热忱对域外理论界隔空进行单向度的表达,而由于各国法治实践及理论研究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些理论努力对法治以及法治意识形态建设并无实际作用。” 因此,有问题意识的法学研究者,在面对诸如此类的话题时,大可不必见到一群外国知名学者讨论得热火朝天便盲目地去邯郸学步,而忽略了哪些才是体现我们自家国情、最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当代的政法体制运作)。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从事法学研究时应当闭关锁国,对国外的学术理论一律加以拒斥。我所强调的是,这种国际视野应当建立在学术的主体性意识之上。事实上,法学研究中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Question)、话题(Problem)和命题(Issue),哪怕是直接来自现实的法律实践,有时在一些相关的西方理论的比照下,可能会变得更为明晰;或者说,带着包括从西方一些成熟的学术理论中所获得的启示在内的理论思维去分析的现实实践,很多时候能够有助于将其在学术传统当中提升为重要的命题,进而可能与西方的学术理论展开平等的对话。例如,自从党的第十八届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党的第十八届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均专门提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后,讨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一话题的文章便在很多报纸和刊物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坦率地说,讨论此话题的很多文章,常常流于宏观而论,在学术欠缺深度。在我看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与现有的学术理论资源进行勾连后加以深入讨论;倘若将“国家治理能力”吸纳进一些成熟的西方学术理论传统当中展开分析,例如由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学者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出来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学说,则可能会发掘出更多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和命题。
四、结语
本文批评了那种按照教科书式体例撰写法学论文的套路,认为其最大的弊端在于往往“有论域而无论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此类论文就毫无价值。在改革开放之后法学恢复和重建的那几十年中,这种教科书式写作体例在当时法学作品生产中的流行,有其客观的时代背景,亦有其特定的时代贡献。
但时至今日,法学论文写作中的这种教科书式写作套路的影响,倘若不能得到扭转和改观,将会造成很多照此模式生产出来的法学产品(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某些专书)长期停留于针对“法制问题”的对策法学研究层面,而欠缺对于从实践中提炼而来、具有理论意义的“法学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推陈出新, 进而极大地影响到法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提升,以及法学研究在国际学术市场上的学术竞争力。而要削弱这种教科书式写作套路的顽固影响,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便是要在法学院所提供的学术训练中强化对于由问题(Question)、话题(Problem)和命题(Issue)三者关联构成的“问题意识”的认识和重视。
请更换成你的二维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