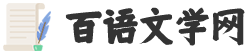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作者简介] 丁元竹,1988年在山东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91年在北京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现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小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志愿活动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社会发展管理》《中国社会建设战略思路与基本对策》《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战略与对策》《交锋与磨合——公共服务提供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的逻辑》等。
摘 要
“现代中国社会学派”这一称谓,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于1938年10月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撰写的“序言”中,对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用小区研究方法开展的系统性实地研究活动和对中国社会及其出路开展探索的一种概括。现代中国小区研究起步于实地中的个案研究,始于“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发起的对广西、山东、江苏、山西、福建等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教育实地调查。这种“社会学调查”与一般的“社会调查”有所不同,它强调社会学的专业性,发现社会的基本规则和原理,坚持体察和定性分析,通过社会变迁了解社会现状,进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石。由于“现代中国社会学派”把人类学和小区研究的方法用于研究现代社会——“文明人”,尤其是由于全球化导致的中国在一个世纪中的磨难与奋争,从而突破了自弗雷泽到马林诺斯基以来人类学专注“土著民族”的研究方法和风格。从弗雷泽、马林诺斯基到“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再到当代人类学,是一个人类学、社会学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不断扩大、不断创新的过程。在21世纪,人类学聚焦全球变迁和全球化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语言、种族和种族主义、民族和民族主义、性别、亲属家庭和婚姻、阶级和不平等、全球经济、、健康和疾病等等,“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在这个进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间人和过渡者的角色。观察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也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和费孝通的思想轨迹中看到其踪影。
关键词
“现代中国社会学派” 费孝通 实地研究
引 言
“现代中国社会学派”这一称谓,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于1938年10月为费孝通(1910—2005)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译为《江村经济》)撰写的“序言”中,对以吴文藻(1901—1985)、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用小区研究方法开展的系统性实地研究活动和对中国社会及其出路开展探索的一种概括。
马林诺斯基在“序言”中写道:“费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内容,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他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在1936年,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访问了伦敦经济学院,马林诺斯基在与吴文藻的交流中得知,“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基于此,马林诺斯基才把这个正在“攻关”的群体称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派”。这也是后辈学者谈及费孝通及“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由来。
本文的目的是想对“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产生、发展进行诠释,并且希望通过梳理这段社会人类学的历史,能对当前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体系有所启迪。
一 “现代中国社会学派”:时代背景与学术共同体
(一)“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学术研究行为的两根支柱
在19世纪,世界许多国家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因此,学习西方、摆脱压迫就成为这些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选择之一。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看法:“面对前途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由改良阵营转向了革命阵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革命时代。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和科学运动,唤起了中国人对民族和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这种探索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由表层讨论进入其内部分析和研究,由理论探索转变为改良、改革和革命行动。换句话说,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的道路,既可以从那个时代面临的挑战和变革中找到它的缘由,又可以从中国社会的文化及其结构中看到它的影子——面对外敌入侵和民族磨难,有血性的中国学者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危机感。而“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世界观、思想风格、理论和方法的形成,也正是近代以来国际上的各种经济、文化、社会思潮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并融合的结果。对此,晚年费孝通看得比较透彻,他写道:“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他们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这个“碰了头”,首先是“东西文化观”,接下来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文化出路、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这种争论继续的背后,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推动民族复兴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百年现代化思潮的演变,一直是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线——中华民族复兴与文化革命的命题及其讨论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中国社会及其文化背景,仅仅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学术研究行为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需要从“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学术研究的环境及变动中去寻找。五四运动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各种激化的社会矛盾,使蜕变中的中国社会陷入深深的危机,寻求中国的出路几乎成为每一个先进中国人的共同要求。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也唤起了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他们冷静地思索着中国的未来和个人的前途。五十年后,费孝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1928年,我毕业于东吴附中……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的一年,我当时在中学读书,跟着许多进步同学闹学生运动。北伐军进苏州后,我参加了当地民报副刊的编辑工作。革命的潮流激起了像我一样的许多青年的热情和憧憬。但昙花一现,革命失败了。许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我安不下心,坐不安了。我想,医生固然能治病,病源却不在个人而在社会,治病人得先治社会,学医既然先学生理,治社会也得先学点社会原理,这样,我才转学到燕大开始学社会学的。
大革命深深地影响了费孝通的世界观。这场革命是费孝通成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开端。20世纪后期,在与美国人类学家巴斯特纳克(BurtonPasternk)的谈话及在许多场合,他都认为,1927年的大革命是他生平事业的转折点。从此,他与千千万万先进的中国人一道,转向了对中国社会出路的求索。
(二)从全盘吸收西方文化转向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
中国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始于19世纪中叶,并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后,“但五四时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新的变化”,就是如何处理西方思想与东方文化的关系。以反全盘西化为标志的新启蒙运动便是在这样的年代发生的。新启蒙运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了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化的讨论。胡适(1891—1962)、陈序经(1903—1967)代表了“全盘西化派”,潘光旦(1899—1967)、吴景超(1901—1968)则代表了“反全盘西化派”。两派的斗争表面上看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问题,即承认不承认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发展道路。
“反全盘西化派”的主将之一潘光旦,对费孝通的影响至深。1930年,费孝通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文藻、杨开道(1899—1981)、许仕廉(1896—?)等人与清华大学教授陈达(1892—1975)、吴景超、潘光旦等人关系密切,而他们中间的联系主要靠两系的学生,如费孝通、杨庆堃(1911—1999)、林耀华(1910—2000)、黄迪(1910—?)等人,费孝通的学士论文《亲近婚俗之研究》还得到了潘光旦的指导。1933年毕业后,费孝通又考取了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之后与潘光旦接触甚多,差不多“每个礼拜总有机会见面,交谈”,从中“看他们怎么生活,如何待人”;从潘光旦身上“不仅学到了做学问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的这一方面的道理”。,。潘光旦认为:“民族的根本问题,具体言之,是一个人口的位育问题。”费孝通说:“我深刻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事情。我相信这几位老师做学问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做人的精神支柱。”
如果说,“全盘西化”与“反全盘西化”的斗争打破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隐含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定——世界发展会趋于统一的模式和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话,那么,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学术上的论战则表明,中国社会科学界已经开始觉醒,从现实问题和现实发展来探索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这些论战对费孝通学术思想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他对这场争论中的方法及方法论问题持有不同看法。1937年初,在致郑安仑(1910—?)的信中,费孝通严肃地批评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式”方法和利用外来理论套用中国社会的倾向: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因为外来书籍文字的输入,以为靠了些国外学者在实地所得的知识,所以用来推想中国的情形。他们其实假定着文化到处都是相同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本身,在我们看来,就是需要加以事实证明的。而且,这假定根本就抹煞了加以详细研究的必要。若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假定的话,不如先认为文化并不是到处都相同的;因为是不相同,所以我们推究它们不同的地方;而同时,亦不敢随意接受不是从本土事实中归纳出来的结论。这样我们可以不必和人家争论中国文化现象是否尚处在封建阶段或是半封建阶段,我们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实地详细它。
他认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中国自身发展的实际入手,而不是用外来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事实;外国的理论是基于国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的理论解释,不能简单套用于中国的发展实际。这种把外来理论和文化通过对中国的实地研究加以解释并修正的思维,推动“现代中国社会派”的学术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现代中国社会学派”是一个学术共同体
伴随着对西方文化模式的反思,从实地研究的角度认识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选择,“到实地去”成为献身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信仰。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社主办的《社会研究》发表了一个宣言,声称:
社会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挽救这沉沦之中的中华民族,我们以为任何可以实行的方案,其规定的办法,一定要根据以明了的事实……社会改革的方案若不根据于广博的社会知识,其造孽的程度将远于小匠造大屋。但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略了。
这一宣言,可视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成立宣言。而《社会研究》,主要是由林耀华、费孝通、黄迪、廖太初(1910—2000)等人负责,他们都是吴文藻的学生。
1990年初,笔者拜访了吴文藻的夫人谢婉莹(1900—1999,笔名“冰心”),在谈到吴文藻时,她自豪地说,吴文藻有四只“狗”,即他的四个学生费孝通、林耀华、黄迪、廖太初都出生于农历庚戌年(狗年,1910)。吴文藻早年就学于清华学堂,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后留学美国。他一方面“循规蹈距地接受了外国科学的那一套”,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在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等人的指导下学习社会学,积累了丰富的国学知识并熟悉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样的训练,为他后来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研究中国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吴文藻年长费孝通九岁,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期间“读了他(吴文藻——笔者注)书架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书”。1952年,国家对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进行调整,吴文藻与潘光旦、费孝通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成为同事,后来又一道研究和翻译世界史。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已认识到,探索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出路,必须从国情入手,因此,他们呼吁:“在中国现在的局势下,我们怕是即使人人都有热烈的情感和忠挚的态度,要改造中国,单因了对于中国社会没有正确和充分的认识,会将达到和希望相反的结果。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这重要性,就是认识国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吴文藻为首的燕大社会学社汇集了一批有志于献身中国社会研究的年轻人。社会学社虽不是一个正式组织,却是一个由有着共同志向、向心力极强的群体,这一点可以从费孝通到瑶山和“江村”,李有义到山西,林耀华到福建,廖太初到河北的行动中看到。《社会研究》发表的《送行》一文中写道:
原野是最可爱的地方,是我们问题的所在,简单结实,那些从前只让太阳和月亮照到的社会事实,现在都在你们手下让你们支配了。世界只有一件事情最乐,发现事实,发现真理,留在后方的人只感到一股酸味儿,恨不能和你们携手同行。
这次行程不叫你们去游山玩水,更不是请你们去欣赏自然,简单说是盼望你们在自己的小区里发现了人群共同生活的通则原理,人和人、人和环境的一切关系。
风啸啸,雨茫茫,愿你们各自保重,请记得,没有苦,没有汗,拿不出成绩,不要你们回来,不认识你们,也无须再见。
或许可以将《送行》视为中国社会科学史上的一首壮歌。如果说,在1935年以前,“到实地去”还是一句口号,那么,从1935年起,这个口号在社会学社变成了实际行动,并逐步变成了一套系统的小区研究计划在实地中付诸实施。人们各自在自己的田野中做出了成绩:除了王同惠(1910—1935)的《花蓝瑶社会组织》、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外,林耀华在实地中写出了《福建的一个民族村》,杨庆堃写出了《山东的集市系统》,徐雍舜写出了《河北农村小区的诉讼》,廖太初写出了《汶上县的私塾组织》,李有义写出了《山西的土地制度》,等等。到达英国后,费孝通依然与社会学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止。后来,费孝通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
二 国际社会学与“现代中国社会学派”
(一)社会学家派克及其中国之行
193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派克(R. E. Park, 1864—1944)访问燕京大学并发表学术演讲。在讲学期间,他声称自己是个“唯实论者”。“唯实论”(Realist)是与“唯名论”(Nominalist)相对立的认识方法,后者坚持人们认识事实必须从事实的概念入手,而唯实论者则认为只有从事实的实体入手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派克是从新闻记者开始其社会学家生涯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特点和学术风格是从体验入手来了解社会及其事实。由此,他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吉丁斯(F.H. Giddings,1855—1931,一译“季亭史”)发生了分歧,产生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方法的两大派:以吉丁斯为首的重统计分析的哥伦比亚学派,以派克为首的重体验的芝加哥学派。派克注重个人的直接经验和经验的交流,认为“凡是经验到的都是真实的,凡是可以交通的经验都是科学”,“这种态度就是詹姆斯之所谓过激的实验主义,所以他的方法,还是由他们的根本观点上发生的”。
派克1889年曾留学德国,就读于腓特烈-威廉大学(Friederich-Wilhelm),在那里他选了第一门课——社会学,教授是齐美尔(G. Simmel,1858—1918)。在齐美尔全部方法论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反的方法:一方面是反对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主张用直觉和经验的方法研究人类行为;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归纳的方法研究社会,使社会学成为归纳的科学。派克还选修了齐美尔的伦理学和19世纪哲学。后来,他又师从文德尔班(W.Windelband,1848—1915)学习哲学并随其转入海德堡大学。文德尔班是狄尔泰(W. Dilthey,1833—1911)的学生,与狄尔泰一样,文德尔班也坚持社会科学的人文方法,并且影响了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派克在文德尔班的指导下,从事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并深受后者影响,后来他写成的博士论文《聚众与公众:方法学与社会学研究》便是一部在德国“领悟”思潮影响下产生的方法论著作。
晚年费孝通又专门研读了派克的传记和著作,自称为“重温派克社会学”,并且不无深情地说道:“在我的学术生命里,‘派克来华’原也是一件偶然的巧遇,并不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但回想起来,这却是一件对我的一生起着关键作用的事。”这个关键作用,既表现在早期派克引领他深入社会现实,也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主张建立“迈向人民的社会学”。
(二)人类学家布朗与燕京大学的中国小区研究计划
费孝通和王同惠赴广西调查后不久,功能派的一位首领拉德克利夫-布朗(A. Radcliffe-Brown,1881—1955)来燕京大学讲学,对中国的实地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这期间,燕京大学社会学社在《社会研究》上撰文,对今后的实地研究提出了设想:“以提倡现代小区的实地研究为标志……考察社会事实,应采取功能的观点,有机的和动进的看法”;一是“想来贯彻这种主张”,二是“推进这个既定的方针”。实地研究是社会学社几年前就确定了的努力方向,布朗来华所讲授的功能派观点及对中国小区研究的建议,对社会学社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就是:以了解中国社会为宗旨,采用功能主义的方法。
(三)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思想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期间,费孝通主要是参加了马林诺斯基主持的“每星期五下午举行的‘席明纳’”。所谓“席明纳”(seminar),即通过“席学、明辨、纳新”的教学模式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费孝通将它模拟为“人类学的前沿讨论会”。了解马林诺斯基的某些思想,可以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观察费孝通关于体察方法的形成与意义。在马林诺斯基的学说中,社会事实被当作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并且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估量、可见的社会事实,诸如人口、地形、人口分布、所有权等。这类事实仅仅是对部落制度和文化分析作出粗略的概述。另一类是不可估量的社会事实。在马林诺斯基看来,人类学家的真正任务是要分析生活中的不可估量的事实。主要有:说话的腔调,交谈时的气氛——敌视和友谊的强烈程度,人们之间的同情与厌恶,虚荣心,等等。这些看不见的事实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像无数细线将家庭、村落串联起来。基于对社会事实的分类,马林诺斯基将研究方法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数量分析。他并不是一个否定数量分析的人类学家,而是一个基于社会事实类型采用不同方法的人。另一类是对被研究对象内心世界的分析。他要人类学深入到被研究对象的内心,在与交谈者一起生活中,了解人们的态度、心理变化。眼下没有材料可以证明马林诺斯基受到了德国社会学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认为他受到弗雷泽(J.G. Frazer,1854—1941)的影响。晚年费孝通回忆道:“如果说马老师是在20世纪初年手执功能学派的旗子,插上英国人类学的领域,成为这门学科老一代的接班人,传递这根接力棒的,我想说,正是当时高居在这角文坛上的大师SirJames Frazer。”但弗雷泽的新人文主义,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É. Durkheim,1858—1917,一译“涂尔干”)的批评。
三 费孝通在“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创立时期的思想
(一)费孝通早期研究方法的阶段性特征
费孝通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开始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术生涯的。尽管他有许多显著的个人特征,但在总体上仍属于“转变的一代”。
费孝通的实地研究问题的思想形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0年特别是1932年派克来华至1936年初。这是费孝通的实地研究理论的确立时期,,以及客观知识的获得“一定要主观的深察体会”的方法,主要表述在《社会学家派克论中国》《人类学几大派》《派克及季亭史二家社会学学说几个根本的分歧点》《亲迎婚俗之研究》《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等论文中。
第二个阶段从1936年起到1937年底。这个阶段,费孝通明确地提出了对“社会研究有坚决的信仰”,并对小区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费孝通关于实地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阐述,不同于那种社会理论形成于实地研究之前,而是在经历了两次实地研究之后。从广西的瑶山回到北平之后,他写下了《社会研究的关键》《论普遍与特殊》《社会研究能有用吗?》《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等论文。从江村来到英国后,他又写出了《理论与实地研究》《关于实地研究》《关于<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的通讯》等。事实上,在进入瑶山之前,他已经初步探讨了实地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其要点是体察以及体察方法与统计分析的关系。
1936年春夏,在读了廖太初的《汶上县的私塾组织》后,费孝通写道:
我读了太初的《汶上县的私塾组织》,更使我对小区研究有坚决的信仰。我们觉得这一篇文字不但证明了我们所有方法和观点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社会现象,而且觉得正确地了解任何社会现象,我们的方法和观点也是最有效、最切实的。
廖太初使用“功能的观点来实地研究一个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私塾。所谓功能的观点,就是把教育看做一种社会功能,教育制度看做相互关联的社会制度之一,它的生长、存在和变化处处是和整个社会相呼应的”。费孝通认为,中国除了私塾以外,其他现象,诸如信用合作、地方行政等,也可以如此方式进行研究。
费孝通关于小区研究的观点是在英国留学期间才成熟和完善起来的。在谈到《江村经济》时,马林诺斯基说:它旨在说明构成江村农民消费、生产、分配、交易的经济体系与江村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小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费孝通认为,小区研究,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有“一个综合的,实地的,对于中国的文化现象的认识”。在这里,他提出了中国小区研究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他指出,“综合的是和分科专门的、各不顾各、片面的相反”,即提倡多种学科之间的相互协作;“实地的,是和凭空捏造的、抄袭的、不足考实的、雇佣‘劳工’间接搜集资料相反”。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须在一个较小的区域中作较久的及较密切的体悉,不多走路、多看码头是不成的。”由此也可以理解,在其晚年他何以“行行重行行”。
(二)费孝通与燕京社会学社
燕京大学社会学社这个学术团体影响了费孝通,费孝通也给这个团体注入了生机,“他的继续不断的努力成了同人兴趣的中心”。社会学社赞誉他是“一只陷阱压不死的活老虎,到处给人奇特和惊奇,他的能力是我们早已知道的,还有那看不见的能量,朋友们都敬重他”。由此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费孝通和他所处的社会学共同体的意义。这个社会学共同体,既影响了费孝通个人,也影响了社会学的发展。理解这个共同体的目标、气氛,是理解费孝通思想风格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20世纪末年,在回顾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程时,费孝通说道:
我对于中国的社会调查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实证方法、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中吸取研究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进而按照自己的认识想方设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发展道路的理解。
这也包括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他在2002年写道:
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这里的“少数民族”思想,可以追溯到他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对于瑶山习俗的解释,表现出他功能主义的倾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其实有着功能主义的思想渊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对功能主义思想的超越。
(三)费孝通早期的理论探索
费孝通的第一篇社会学论文是介绍派克与吉丁斯的,即《派克及季亭史二家社会学学说几个根本分歧点》。文中有一部分专门探讨二者的方法:“季亭史重统计,而派克认为统计方法不足以完全解释社会现象,故重个例方法。”费孝通认为,吉丁斯和派克在方法上的分歧,导源于他们的社会观。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费孝通对派克情有独钟。他写道:
派克并不是要排斥统计方法于社会学之外,只是认为统计方法决不是社会学的唯一方法。社会学的对象即在社会态度,而社会态度是变动不居,没有一个不变而一致的单位可得,自然无从统计。于是他提出个例方法,尤其是个人自述经历视为社会学最宝贵的材料。
派克之所以注重个例,是因为“个人生存社会中,一切行为和态度都在不自觉地态度中发现出来”,“这种个人平时不自觉的态度是社会所共有的。个人只是一般的例子。在一个人的自述中,就能得到同一社会中一般人的态度了。所以,个例研究并不是个人主义者的研究方法”。费孝通认为:“统计方法是在求许多个体中的多数,个例方法是在从一个人的自述中发现一般的态度。前者才是最个人主义的方法,后者实是集合主义者的方法。”在费孝通看来,派克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有效途径,“因为他所给人们的不是普通的知识而是生命,一种能用以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并非单由客观的描摹可以获得,一定要有主观的深深体会才能得到,所以我说是生命”。对此,美国衣阿华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阿古什 (R.David Arkush,汉名“欧达伟”)评价道:“正是派克将费孝通从图书馆解脱出来。”不管他说的是否准确,但至少费孝通承认,派克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能把他的学生从书本上解放出来,领到一个活的世界中去领悟人类生活的真相,这是他在社会学界中树下百年基石的工作”。派克的魔力不仅表现在他访问燕京大学期间和对燕京大学师生的影响,也表现在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同样激励他的学生和同事到实地中开展社会学研究。他独特的经历,使其社会学理论也尽显特色。
1933年下半年,在《杨宝龄的〈美国城市中俄籍摩洛根之客民〉》一文中,费孝通将派克的个例方法作了进一步发挥。首先,他认为文化的研究不可能全部采用统计方法,尤其是不能用统计方法推测社会的内部结构:“由统计推测社会内部时,就有种种困难,因为要从甲推测乙,先就需要肯定甲与乙的相关系数,而这种相关的甲与乙若有一是不能以数目表示的时候,分数就无从确定。”其次,许多甚至大部分社会事实是统计方法无法测量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甚至最重要的地方是无从统计的,因为统计需要不变的单位,而社会现象中要求的这些单位是不容易的,有时是不可能的。”“如社会态度、人生理想的变迁只能加以描述,而决不能归原于可统计的单位。”这里隐含了费孝通的一个重要观点:以个体为分析单位的统计方法,与以整体为单位的人的行为和态度分析方法是冲突的,因而采用计量个体的统计方法来分析集体行为是不可能的。他的方法与他的社会观保持了一致性。
费孝通是在广州得知布朗来华讲学和社会学社小区研究计划的,他在致林耀华的信中写道:“最近才听到燕京有民族学方面发展的计划,——若是同惠迟死一月,她要多少快活呢?”吴文藻把功能方法规定为小区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提出:小区研究是“在一个特殊小区之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密切的相互联系,而为一个整体,或体系中的各部分,在研究任何一方面,必须研究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这就是说,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它的功能;而且只有发现它的功能时,才能了解它的意义”。后来,费孝通写道:“关于小区研究的名词的好处和意义已有吴文藻先生几篇文字的解释,我想大家一定是有了解的。”吴文藻倡导的中国小区研究计划对费孝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小区研究方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吴文藻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费孝通和他的同学践行了小区研究的方法,“现代中国社会学派”从其产生起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
费孝通坚持体察方法的另一个动因是他的社会整体观。他认为,在社会尤其是文化研究中,只有将社会与文化当成一个整体,深入其中体悉,才能客观地描述它。他写道:
当一个生长在社会变迁率较高地方的研究者,到一个和西洋文化接触较疏远的小区中去,因为当地的变迁率较低,积久传统下来的社会制度经长期调适,他很自然会发生“结构微妙”的欣赏态度。这对于研究者没有什么妨碍,因为在社会研究的第一步工作是在发现文化部分间的关系,和它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
费孝通在这里已经将体察的方法引申到如何来理解一个体系及其结构关系的层次上,从而也使得问题变成了方法论的问题。从这个方法论问题上,又可联系到迪尔凯姆与韦伯在两种研究方法上的争论,即现代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之争。以反实证义主著称的韦伯主张,社会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被研究对象的意义。韦伯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旨在外部的、事实的描述和因果律的解释,后者则是与对文化现象的内在意义的移情的、直觉的理解。迪尔凯姆是早期实证主义的最大代表,在社会学研究中,他另辟蹊径,即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致力于所有科学的统一,他反对内省理论,认为内省是个人意志的、主观的,个人内省仅限于心理现象、精神性,而无法了解社会事实的超精神性。在早期的学术活动中,费孝通曾专门研究各派心理学中的内省问题。这说明,费孝通对贯穿于社会研究方法论中的基本问题早就注意到了,而且做了深刻的思考和研究。他也曾考察过这两种方法的渊源。
结 论
现代中国小区研究始于实地中的个案研究,始于“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发起的对广西、山东、江苏、山西、福建等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教育实地调查。这种调查“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后来被马林诺斯基的学生弗雷德曼(M. Freedman,1920—1975)称为“微型社会学”,专指马林诺斯基所说的“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在中国社会学界,也有人称之为“社会学调查”——强调社会学的专业性,发现社会的基本规则和原理,坚持体察和定性分析,通过社会变迁了解社会现状等等,以区别于一般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和王同惠的瑶山调查,奠定了现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石。小区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学术共同体——燕京大学社会学社以探索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为己任在实地中的学术实践。
“现代中国社会学派”把人类学和小区研究的方法用于研究现代社会——“文明人”,尤其是由于全球化导致的中国在一个世纪中的磨难与奋争,从而突破了自弗雷泽到马林诺斯基以来人类学专注“土著民族”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在全球视野中审视中国的一个个村庄及其社会变迁,这也恰恰是马林诺斯基所欣赏的和称之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重要缘由。从弗雷泽、马林诺斯基到“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再到当代人类学,是一个人类学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不断扩大、不断创新的过程。在21世纪,人类学聚焦全球变迁和全球化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语言、种族和种族主义、民族和民族主义、性别、亲属家庭和婚姻、阶级和不平等、全球经济、、健康和疾病等等,“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在这个进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间人和过渡者的角色。
。20世纪30年代后期,费孝通继续高举实地研究的旗帜,。这个时期,费孝通将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课程的讲义编写成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领导了云南的实地研究,写出了《云南三村》等著作。,清华大学复校,费孝通与清华大学的师生学习、研讨,编写了《中国士绅》等。1979年,受中国委托,六十八岁的费孝通受命恢复社会学,他提出了“迈向人民的社会学”和“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方针,指导了“小城镇与城乡一体化”、边疆民族地区开发等重大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深入文化反思的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想,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内容。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建设,都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现代中国社会学派”中看到其踪影。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7年第2期第272—283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到本公众号界面下端的“全部论文”栏目点击、浏览。
责任编辑:田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