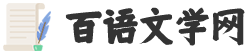学人访谈
本期嘉宾 · 李辉
李辉,,复旦大学“廉政与反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当代的与廉政建设、国家民主转型与政府绩效、族群冲突的比较研究等。2012年参与创建了“五角场学派”,。
,量化方案是否具有更大的优势??如何利用司法裁判文书数据库进行问题的研究?怎样?“五角场学派”是一个怎样的学术共同体?,希望能帮助读者加深对与反、。
: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学术的魅力让人心驰神往,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科研之路的?是什么吸引了您,并让您在学术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的前进?
李老师:其实走上学术之路的原因我个人也说不清楚,回想起来大概主要是受老师和同学的影响比较大。,第二年分专业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上专业课的时候人数太少,许多老师都把上课的方式改成了阅读讨论式,这种上课方式对我影响很大。能在课堂上就某个问题或者某本书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不只是听老师讲他的个人见解,这种课堂给我很大的参与感,也比较能够刺激我思考一些问题。虽然现在想起来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非常幼稚,但当时老师都是非常包容的,非常鼓励我们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时间久了就爱上了读书、讨论和思考,这大概是走向学术道路的起源。不过喜欢读书和思考与能够独立做研究还是两码事,我一开始会天真地把二者等同起来,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读书和思考能让你了解很多人的观点,了解的观点越多,批评一种观点也更容易。但学术研究不等于学术批评,做研究需要你更冷静且全面地思考一个问题,突破已有的解释,提供有创见的答案,更重要的是,你还要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论证自己的答案。
所以其实一直到读博士,我都是停留在读书和思考的阶段,直到博士一年级参加了学院一个暑期调研项目,内容是观察上海市居委会的换届选举过程,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研究。当时的指导老师刘春荣以及我的博士同学熊易寒,在这个调研项目中给予了很大帮助,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自己第一篇学术论文,并且成功发表。这个经历实际上对我是莫大的激励,因为这件事让我知道我有能力做一个研究出来,虽然算不上多好,但至少自己给自己证明了这种能力,而且整个过程让我很快乐,也很有成就感。后来就慢慢喜欢上了做研究,与同行交流学术观点,写论文,发表论文等等这些所谓的学术生活。
: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代的与廉政建设,据了解您擅于用定量方法研究问题。请问您认为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问题有什么优缺点?对于定性研究方法进行问题研究您持何种态度?
李老师:我真不敢号称自己擅长定量,我懂一点,能用简单的定量方法做研究,但我不擅长。原因很简单,我从本科到博士,都丝毫没有定量研究方法的训练,我的博士论文只用了定性方法,而且是单一案例研究。之所以后来逼着自己去学习定量方法,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受制于研究这个话题,做质性研究比较困难,参与观察就不用说了,基本不可能,就连做访谈也很困难,虽然能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一些一手材料,但随着研究议题的扩展和时间的推移,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必须要掌握多元的方法;二是看到大量高质量的研究都是定量的,如果不懂方法,别说用定量方法做研究了,连这些主流的前沿文献都看不懂;三是拿到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正好可以有一年的时间来学习方法。实际上后来证明,一年时间是不够的,但是给了我一个自学的基础,后来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又自己学了一些方法,不过只敢说一知半解。
关于这一话题,定量和定性方法只能说各有利弊。定量方法的弊端很明显,因为“”本身测量起来非常困难,现有的知名数据,比如CPI和WGI,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主观评价上的测度,已经遭受了很多批评,这里就不赘述了。如果“”本身不能被量化,那所有的相关研究都失去了根基。但定性也好不到哪里去,是一个敏感话题,与别人讨论这个话题会天然地引起警惕,所以除非有特别的途径,也很难深入事件中心进行过程追踪。因为这两点,我个人成了一个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者,我觉得要从你研究的问题和可行性来有策略地选择方法,而不是拿着方法去找资料和问题。所以我定性和定量方法我都做,我觉得像这种研究议题,只能是不断地从碎片式的研究中拼拼图,经过长期的积累慢慢勾勒出答案的轮廓,想要使用一种高明的方法一锤定音,终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夺取反斗争压倒性胜利。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候补委员43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多人,处分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形成了反斗争压倒性态势。但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流传着一种“越反越多”的看法。请问您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形势的变化?,专门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确立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关于监察法立法和监察体制改革您有何看法?
李老师:关于近年来反的形势,实际上官方有固定的说法了,那就是从形势严峻复杂,到反逐渐形成压倒性态势,“三不腐”中的不敢腐基本实现了,不能腐和不想腐是下一阶段的主要目标。监察体制改革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在反制度上最大的一次改革,因为自己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这一块,所以也特别关注了这一变化。不过目前还只是停留在观察的层面,没有特别深入的去了解,也没有特别独特的想法。相比于以往的纪检监察加的格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优势在于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的全覆盖,并且集中了反力量,我想的人员加入到监察委之后,反的能力、技能和专业化水平都会有所提升。这样监督权的设立也更加合理,对于提高监督效能有所助益。成立监察委的另外一个意义是理顺党纪和国法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是在理论层面上的,也是在实际执行层面上的。纪委虽然一直被认为的核心反机构,但是纪委再强大,也只能执行对中共党员的纪律约束,在新修订的纪律条例出台后,纪律和法律对党员和公职人员的约束范围已经基本分开了,在法律层面已经有所规定的内容,新的纪律条例不再重复。这意味着在执行的过程中也需要两套机构,监察委与纪委虽然合署办公,但是职责、权限和办案的法律依据都完全不同,惩治和监督的对象也不一样,二者相互配合才构成完整的特色的反机构。
: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然而有些涉案金额、自首立功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判决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引人深思。?司法裁判文书数据库的建立对于问题的研究有何意义?对于数据库的使用将会朝着何种方向发展?
李老师:这个是我最近在着重研究的问题,为此专门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编码了7000多个判决书。从对这个数据的初步分析来看,相同金额的案件,确实处罚的程度有很大差异,这背后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由于论文还在写作过程中,许多结论不方便提前讲,但是可以稍微透露一点。我们发现,金额和情节还是决定判罚程度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金额。但是金额与判罚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为300万元以上,处罚力度都一样,差不多是无期到死缓,所以贪更多反而等于处罚变轻了。另外,有减刑情节的案例,处罚程度都显著降低了,但是有加重情节的案例,却并没有显著提升刑期,这是因为几乎所有有加重情节的案例,也同时获得了减刑情节,二者作用抵消了。最后,我们还发现集体的窝案,实际上参与者的处罚也比个体更低,因为总金额被分摊到主犯和从犯身上,平均下来每个人的处罚并不高。
司法裁判文书数据为研究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而且量特别大,为我们用大样本检验一些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使用这一数据也要注意很多问题。一是无法号称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抽样数据,因为在一定的时间窗口里面,每个地方上传的文书数量可能完全不同,同时在下载使用的过程中也会有所遗漏;二是将纯文本数据清理编码的过程非常艰辛,而且很容易出错,定量研究讲究数据的精确性,一旦编码错误,满盘皆输,而且会得出有误导性的假结论;三是数据本身在许多基本的人口学变量上缺失严重,为后面的分析带来很多麻烦。但是这一数据依然有进一步挖掘的意义,我目前关注其中两个重点问题:一是的结构性特征,就是不同地区自体(贪污挪用类)和交易型(行贿受贿类)的构成,到底有哪些因素决定了这种结构性差异;二是的金额问题,什么因素决定了案件的金额,是个人手中的权力还是其所在地区的环境因素。
:我们了解到,您在潜心钻研问题之外,。您和唐世平、熊易寒等几位老师于2012年共同创建了“五角场学派”,,并试图探索发展家未知的研究领域,从而更好地迎接现代化。您能为我们介绍“五角场学派”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接下来的研究规划吗?
李老师:我可不敢号称是“五角场学派”的创建者,创建者当属唐世平教授,我只能算是其中比较积极参与的一位普通成员。这个参与的过程其实也是跟着“学派”中许多优秀的前辈和同辈学者学习做研究的过程。五角场学派算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术共同体吧,我们基本只探讨学术,大家会相互传阅各自的论文,交流自己的研究心得,年终会自发开一个纯学术的研讨会,报告论文并相互批评。虽然大家的研究领域千差万别,但对社会科学以及如何做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基本的共识,大家在这个基本共识下一起努力,相互鼓励,在这个过程中共同成长。我从“五角场学派”学到了非常多,。不过我们很少有真正的集体成果,大家的学术合作也是根据研究领域和兴趣自发形成的,要说集体成果的话,,大部分学派成员都参与了,各自贡献自己擅长的一块研究。
:有人说,,鲜有对于域外其他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您有何建议?
李老师:,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千差万别,想要科学地比较谈何容易。,,,在根本上还是要回答问题,所以很自然拿与其它国家比较。这跟托克维尔在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时候,。但是就我所知,目前这种情况也在不断改变,许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新秀学者,都有着自己专注的研究区域,比如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我看他们的研究也没有特别去拿进行比较。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觉得要敢于开拓自己的领域,现在全世界对都很重要,有大量的海外利益,我们需要了解世界。,眼光不要只盯着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们了解到,您最近在构思一本新书,大概今年年底出版,请问可以先给我们读者透露一点新书的内容吗?
李老师:新书的主题是“”,之所以想写这本书,原因在于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一个问题,,包括官员、。。,,但实际上从定义到测量,。,使得研究越来越难以满足解决问题的要求。,,。
本期采编:龙雨葳
,个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网站链接;媒体转载(包括网站、微博、。识别二维码可添加编辑团队微信。
支持学人原创
| 学人专访系列
、实践品格与立体图景式 —— 对话清华大学任剑涛教授
学者当自树其帜——对话南开大学李春福副教授
如何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与科学化?——对话南京大学梁莹教授
? | 对话人民大学李石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