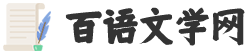不少著名学者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完成博士论文才是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这句话颇有道理,因为只有经受博士阶段的专门训练才可能在学术起步上跨出质变的一步。但我觉得,不能想当然地由此推出,硕士论文的撰写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创作、无需严格遵循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无论是否继续攻读博士,我想硕士论文的写作对于一个追求优秀的研究生来说,意义重大。论文的写作不仅锻炼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提升写作水平,也极大地磨砺个人的意志、培养一种愈挫愈勇的毅力。
记得16年论文开题时,我的硕士导师张凌教授十分负责地帮每一个指导的学生把关论文的选题和提纲思路,即便有同门尚在加拿大留学也通过视频实时地受到了指导。我在提交第一次提纲时,拟定题目为“故意犯结果归责中回溯禁止”的成立范围,由于“回溯禁止(Regreßverbot)”理论在我国刑法学界研究较少,尤其在故意作为犯中很少被提及,因此我想选择这个题目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此外,也因为研一期间撰写有关“客观归责理论与过失犯论”之类的论文时,搜集过不少相关资料,于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节省了一些时间。然而,当我兴致冲冲地将选题发给导师时,得到的回复却是——题目及框架德国法色彩过于浓厚,所用术语与相当因果关系等传统理论到底是何关系,需作出平义的说明。后来,,他也指出了这个问题:例如答责性、自我答责这样的词语最好转换成国内学者能够接受的词汇,因为毕竟是写中国刑法方向的论文、也申请的是中国的法学硕士学位。实际上,我的写作初衷是将“回溯禁止”在故意犯中的有关理论及其运用在论文中作系统、详细的阐述,但我也意识到“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且考虑到相关德文资料收集实在困难,遂而改变方向,转以国内外方兴未艾的“介入因素与结果归责”为主题,在故意作为犯中予以展开。
不过,这才算刚刚开始。虽然我不再单纯对“回溯禁止”作研究,但“介入因素下故意犯的结果归责”中仍然需要介绍这种很有影响力的归责思想,并且需要理清它和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于是我还是尽力搜集这方面的中外文资料。当时能看到的国内期刊中,明确以“回溯禁止”为题的只有何庆仁教授的一篇论文(“溯及禁止理论的源流与发展”),但他的注释当中却指引了很多相关的德文文献,于是我就顺着他的注释对德文文献进行收集和筛选。由于德文文献很多不上网、且我国即便是顶尖的几所大学也没有购买德文数据库(如ZStW等),所以这件事只能求助于德国在读博士生。幸运的是,正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的郑童师姐以及在波恩大学的蔡仙师姐、吕翰岳师兄抽出宝贵时间、给我扫描了急需看的一些资料。另外,和我一起长大的发小俞宽(正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攻读计算机学位)更是不遗余力、给我发来几本完整的德文专著,并在过年回家时给我买来了Roxin、Puppe等教授的教科书。尤其是Puppe教授在事实因果与结果归责上的一些论述,给我的问题思考吹来了不少新鲜空气。
研三开始之后,我就着手阅读这些文献。当时觉得阅读文献是一件十分难熬的事情,因为我刚完成德语B2的课程,对于德国刑法学上的专业术语及表达方式都不熟悉,看起来非常费劲,且往往不知所云,心情起伏很大。好在,由于近年来国内学者大量引进客观归责理论、对于结果归责问题也正在进行不少功能化的思考,所以有时看看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也较能辅助问题的正确思考。不过,9月份突然到来的清华大学博士申请考试,突然打断了我的节奏。8月底的时候我决定报考清华,按申请制的要求必须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初稿”——可是当时只剩下十五天!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开始写作。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了将近四万字的初稿,其低质量可想而知!当然,前期的阅读工作毕竟打下了一些基础,才使得论文的基本框架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博士录取之后,再度开启写作的日程。由于初稿已出,突然像是对接下来的写作感到迷茫,于是就在跟博士导师的闲聊中谈及此文,恳请提供宝贵建议。博导特别组织硕士生对于我的论文进行了讨论,觉得我的基本思想值得肯定,但由于写了好几个方面的问题,文章显得范围太广、缺乏主线,研究也不够深入,于是建议我只选取其中一块内容重新来展开。我本来要在“回溯禁止”中讨论故意作为犯、过失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三个领域的归责问题,听了老师的建议后,决定只选择研究较少的故意作为犯领域进一步研究,探索故意犯归责的机制和介入因素的问题。
在重写的第二稿出来后,过年回家时我又阅读了一些文献、再次进行大修。但是冬天的寒冷却让我的文章后半部分走入一些歧途,写作过程反反复复,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在后来的写作中,我重点对国内学者追捧的相当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相当性只能界定实行行为,客观归责理论在故意犯中捉襟见肘”的论断,并给予了充分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我在文章的核心部分重点阐述了故意犯和过失犯在不法类型和归责机制上的差异,并由此澄清了客观归责理论可能对于故意犯归责产生的误解。对于故意犯本身的具体归责标准,在检视了德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说之优劣后,我提出了以“意志支配”为核心的归责标准,并就不同介入因素类型给出了大致的结论。
在撰写文章的建构性部分时,我主要参考了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周漾沂教授的主要思想,他的文章一般都很长(多达五六十页),但其清晰的论证常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启发。并且,周教授是台湾“科技部”【结果归责理论的反省与重构】科研项目的主持人,在这方面是专家,所以我斗胆将自己的第四稿发送给他,并表达了求教之意。几天后,周教授十分客气地回复了如下内容:
喻先生您好,我讀過了您的文章,您的文章思路清晰,論證有力,最後採取的主觀歸責立場也為我所認同,實在很難給您什麼進一步的意見。
如果勉強要說,可能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在論及Puppe故意危險理論的部分,所謂故意危險的確定,究竟是從行為人觀點還是客觀第三人觀點,煩請您再稍微確認。文中談到Y知道Z身患血友病之例,倘若是從行為人的觀點確定故意危險,那麼Y持刀劃傷Z,的確是使用適於導致死亡的方法,創造了故意危險,與您從客觀角度而言未創造故意危險的說法有所歧異。
二、我個人區分「主觀歸責基礎認知」與「故意」,認為前者是支撐法不容許風險之事實的認知,後者是在該認知內所產生的風險意識,而以主觀歸責基礎認知決定主觀歸責範圍,並切斷了故意與主觀歸責的關係。這種看法不能認為是一種(如您將我歸類的)「規範化的故意概念」,因為所謂規範化的故意概念仍未切斷故意與主觀歸責的關係,建議或可刪除「以規範化的故意概念(取代心理學的故意概念)……。」等句子。
三、您採取「故意支配」概念作為主觀歸責基礎,需要澄清的地方或許在於,您是否徹底切斷主觀歸責與故意的關係,還是仍讓主觀歸責範圍取決於故意。您談到行為人有「抽象預見」時成立故意支配,似乎還是未切斷兩者關係,從認定行為人是否「預見」的心理狀態來決定故意,並依此決定主觀歸責範圍。不過您又提及「在規範評價上只要行為人實際認知到其行為和所存在的客觀條件」就可認為有抽象預見,而無論其事實上是否預見,這種看法已經趨近於規範化故意。不過,到底要說是主觀歸責基礎認知還是規範化故意,都只是用語問題,觀念上都是一樣的,就是必須從規範的角度來決定主觀歸責範圍,這一點也正是我主張以及贊同您之處。
另外,隨信附上我2014年的一篇文章「風險承擔作為阻卻不法事由-重構容許風險的實質理由」,其中對於客觀歸責中的非容許行為理論有些探討,也請您參考並指正。
我十分感动他能够看完这篇4万字的论文,并谦逊地提出这样实质的建议,显然,我对于他存在一些误读,也得到了他的一定认可。在随后的修改中,我根据他的建议进行了调整。文章的第五稿作为定稿、正式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优秀评级。博士导师鼓励我再次修改、尝试投稿,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博士处女作。
如今,那段辛勤耕耘的时光早已逝去,伏案写作的时刻却历历在目。记得自己没信心的时候,偶然间找到了一本叫《法益理论的宪法基础》的专著,翻开一看,,作者叫钟宏彬,当年已经前往德国洪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该文长达几十万字,参考了近百篇中文和德文文献,对于法益理论和宪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学术梳理。看着他的硕士论文,感受到他的付出与执着,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难怪他的导师许玉秀教授会给予他这样高的评价——宏彬以他的天分和努力,就法益理论,在刑事法、甚至宪法领域,为台湾留下一份十分珍贵的学术资产,,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不知道自己的表现以后是否可以让导师感到欣慰呢?
但,博士处女作的发表也仅仅是一个起步。大多时候,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面临着怎样的危机。这篇论文之所以能进行到目前这个样子,不得不说是研究生三年持续钻研的结果。和国内大多数刑法学研究生一样,初上研究生时,我基本同时面临恶补刑法学理知识和开始训练学术论文写作双重的任务。当你写作时,你往往渴望有时间来阅读更多的著作,因为“书到用时方恨少”,而当你阅读疲惫之时,你又得通过写作来发现问题、阐述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井然有序的安排,只有不断地协调各种需求之间的矛盾,保持方向的清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逐渐选择将刑法基础理论中的“归责问题”作为自己的兴趣点和主要钻研方向,因为不可能妄想什么都看、什么都能写出好文章。可是,我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刑法解释学、总则的分则运用方面、量刑理论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知识空白,直到现在这仍然是令我焦虑头疼的问题。此外,在法理学、,也已经让我感受到了瓶颈效应。刑法学的魅力,或许恰恰不在于它那精确的逻辑和体系,而在于它总是反射出背后的社会变迁和转型、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总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疑问。
写于2017年11月2日金秋的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