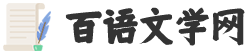上帝选择了一批人,让他们从事叫作文学的神圣事业,而却吝惜地只给了他们最原始、最笨拙、最需要付出心智和精力的生产方式,而且用十分挑剔的眼光去评判他们的创造性劳作,于是文学创作最终成了愚人的事业。
这段话最后的结论是柳青做的。柳青是过来人,有资格发表结论性概括。路遥既崇拜俄罗斯及苏俄文学大家的作品,也崇拜身边的前辈作家——柳青等一批作家,他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从事了只有愚人才肯从事的事业。
因为《人生》获得的成功,路遥是陕西乃至全国文学界作家队伍中的领先者。这让从小个性要强的路遥,大大吐了一口气,这是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领先者必然被追逐,被簇拥,同时,领先者路遥欲往何处,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命题,这命题让他不敢享受成功的喜悦,很快又开始艰难的跋涉和远行,因此他又一次陷入孤独。
现在,路遥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这个意识变得强烈而且相当明确——要把早年富有浪漫色彩的幻想变为人生的现实。
为什么把目标定在40岁以前?路遥说这话时才30岁出头,身体也健壮如牛。
路遥与人谈起这个想法时,举出许多伟大的作家为例,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40岁之前完成的。而且,他还发现,曹雪芹和柳青这两个他非常崇拜的伟大作家,均留下了未完成巨著的遗憾。柳青长篇巨著《创业史》原计划要写三部,100多万字,后因“文革”开始而被迫中断。加上后期柳青的身心备受摧残,壮志未酬身先死,使广大读者无限惋惜。路遥说他必须要在年轻力壮精力旺盛时完成一部大书。
在路遥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这个大胆的想法,让路遥激动不已。但是,想象容易,决断也容易,真正要把想象和决断变为现实却是无比困难的。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千山万水。
路遥面临的困难是各种各样的。他知道,他首先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长篇小说创作的经验。在此之前,他创作的最长的作品就是《人生》,是13万字。即使是这样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当初也让他感到如同陷入茫茫沼泽地而长时间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长篇作品,甚至是长卷作品,路遥很难确知自己能否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企图退缩的路被路遥自己堵死了。
他对自己说,只有以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从1982年到1983年,路遥“平静而紧张地”开始了《平凡的世界》前期的准备工作。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远离喧嚣的采访,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
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路遥首先列了一个近百部长篇小说的阅读书目。这些书,有的是重读,有的是新读;有的要细读,有的仅粗读。尤其是要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多部头长卷作品。
在路遥阅读的多部头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他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这次有目的的阅读,路遥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的是《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路遥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同时,路遥还阅读了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还有一些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的专门著作以及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关于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知识的读物,路遥也不放过地找来阅读。
那段日子,路遥的房子里到处都摆放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卫生间,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
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得差不多了,甚至使路遥快要受不了了,他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根据他的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于是,新一轮的阅读又开始了。为了更清晰、准确地把握这10年间的时代背景,路遥找来了1975年到1983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我开始了这件没明没黑的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
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历时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到1984年,路遥的这部“规模很大的书”框架确定下来了:
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背景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
完成了书写这部“规模很大的书”的阅读准备,此时,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深入生活。路遥打点了行装,他要回到陕北,回到他热爱的黄土地上,开始他计划中的体验生活。他写小说,像新闻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感受。
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路遥开始在陕北各地奔波。各种各样的生活都能令他感兴趣。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他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他再一次深入进去——路遥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倍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他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他认为,故事是可以编的——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用笔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作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新增家养或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
路遥的体验生活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身体力行。他在山上放过羊,在田野里过过夜。来到延安时,他还与新婚蜜月中的刚刚在延安报社做了记者的四弟王天乐一起,来到延安市的东关。两人穿上了一身破旧的衣服,装扮成王天乐当年在延安东关揽工时的样子。很快,他们就被延安沟门的一个工头招去了。因为王天乐当年揽工时肯吃苦,肯出力,名声好,所以,工头一眼就认出了王天乐。
兄弟俩一连在工地上干了三天。路遥干活不专业,一共挣了30元钱,还被扣掉20元。两人三天挣了50元钱。哥儿俩回到宾馆洗了热水澡,赶快将破旧衣服脱掉。因为延安的熟人太多,真的遇上了,不好向人家解释。50元钱挣得很有纪念意义,路遥对四弟天乐说:“咱俩现在一起去邮局,将这笔钱寄给父亲去。”
——关注人和人的命运
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路遥基本上都不再参与,生活处于封闭状态。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路遥也一律婉言谢绝。就连1984年12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作为陕西代表的路遥,也请假没有参加。但是中国作协陕西分会的两个文学活动,路遥还是抽出身来参加。用他的话说是“怀着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个较欢愉的社会活动”。
第一个活动是1984年3月22日至27日,当时是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在西安召开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
在这个会上,路遥做了专题发言——《对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几点认识》。他说,对于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关注人和人的命运,在一切变化中,人的变化,包括人的情感和心理的变化,是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在当前大变革的农村,农民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是需要作家用全副精力来研究的。同时,关注当前农村生活,应该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还应该有穿透未来的能力。
在这次发言中,路遥再次提出了“交叉地带”这一概念,他认为,当代农村生活呈现出一种复杂交错的广泛地相互渗透的状态。这种状态,已大大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要反映今天的农村生活,不了解和不熟悉城镇生活,就可能受到一种局限。
1985年3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优秀文艺创作表彰大会,对陕西省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文艺作品的作者给予奖励,受到表彰的青年作家有路遥、贾平凹、李凤杰。同时,省政府还决定,对陕西省近年来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路遥、贾平凹、吴天明、李凤杰等作家、艺术家给予晋升两级工资的奖励。
路遥参加的第二个“较欢愉的社会活动”,是1985年8月20日至30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采取边参观访问边座谈讨论的方式,在延安和榆林两地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书记处书记李小巴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作家、编辑家、评论家还有贾平凹、陈忠实、京夫、董得理、白描、子页、陈泽顺、子心、李国平、孙见喜等30多人。会议的宗旨和议题是了解近年来国内外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和发展概况,分析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势及落后的原因,制订陕西三五年内长篇小说创作的规划与设想。
这次会议与1980年在太白县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相隔5年,5年时间,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那次参会的作家们,也有了许多变化。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进入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1985年4月21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召开了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三届二次(扩大)理事会,通过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四位理事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此外,会上大家还提到,京夫、邹志安等作家纷纷在全国获奖,还有一批青年作家正在成长。
但是,与会者依然心存担忧。一支实力雄厚的陕西作家队伍虽已形成,粉碎“四人帮”以来,陕西的短篇小说创作同全国文学发达省市大体上处于同步状态,但后来,当一些省市的作家纷纷在中篇小说这块领域进行开拓耕耘的时候,陕西的中篇小说创作从总体上看,却还处于发端之时,可以说是慢了半步。近一两年来,全国长篇小说创作逐渐繁盛,陕西同其他省市发展的情势相比,似乎又迟缓了。在第一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陕西均无作品推荐,陕西省长篇小说创作至少在目前仍处于劣势。陕西的小说家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承认这个事实,并应发奋努力去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
路遥在这个会上,又发表了很独到的见解。他说:“小说,尤其是长一点的作品的创作,考验作家的,不是艺术上的东西,而是作家观察生活的着眼点和理解生活的能力,作家仅‘一度进入生活’还不够,还要‘二度进入生活’。‘一度进入生活’,凭艺术直觉,可以产生激情;‘二度进入生活’,则可纠正前者的片面性和对生活的表面的倾向性,用理性眼光去观察生活,保持作家的‘中性’状态,以便更接近生活本身,更接近真实。就是说‘二度进入生活’可以产生冷静。好多作品没有绝妙的东西,就因为作家没有‘二度进入生活’的深刻认识。”路遥还说,近年来国内长篇小说并没有给他带来满足,他没有这种印象。
这次会议,对新时期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路遥实际上已经投入关乎他终生事业成就的“大决战”当中。这次会议是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一结束,路遥就“神秘失踪”了,他马不停蹄地赶赴铜川鸭口煤矿。几天前一份中共铜川矿务局委员会组织部文件,以《关于路遥同志任职的通知》的形式,发往了省煤炭厅组干处、铜川矿务局机关各部、委、处、室以及公司。通知内容是:“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路遥同志需来我局进行较长时间体验生活搞创作,为了方便工作,根据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党组建议,经中共铜川矿务局委员会1985年8月21日常委会议研究同意:路遥同志兼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全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便条件。
路遥主要体验生活的地点,在鸭口煤矿和陈家山煤矿,他在矿区跑了好多地方。鸭口煤矿,应该是路遥住的时间比较长的,且对整个矿区了解比较多的。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到的“大亚湾煤矿”,就是鸭口煤矿。而且,他作品里面好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就来自矿区。
路遥在鸭口煤矿,没有在吃住方面提任何要求,而是一到矿上,就要求下矿井。他要和矿工们一起劳动,与矿工交朋友。头上戴着一顶矿灯,穿着一件破旧的满是煤灰的工作服,脖子上也学着采煤工的样子,扎一条白毛巾。这时候的路遥,活脱脱一个采煤工模样。他跟着工人乘上下井的升降罐笼车,一个罐笼里有12个工人同行。
罐笼飞也似的顺着井壁向下降落,像从一个黑洞里猛然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对罐笼无法克制的恐惧和厌恶,肯定会时刻伴随着矿工。井壁向外流着沥沥的水,抬头向上再看井口,小小的一个矿井口,像黑色天穹上的一颗星星。
人好似在向地心深入。一分钟后,在离地面大约250米处,罐笼停下来。走出罐笼,站在铺着铁轨的宽宽的巷道里,眼前是向外渗着水的井壁和木头支撑的采煤掌子面,再往深处,就真的是在地心行走了。路遥和工人们在工作面爬着行进,汗滴在掌子面。走在危巷深处,那种感觉,不是苦和累的考验,而是生与死的考验。
当路遥拖着沉重的步子,浑身无力来到搭车的地点,罐笼又像井中提桶般迅速上升。走出井口,浑身煤灰和污秽,人们竟然不能认出他是谁了。路遥学着矿工们的样子,坐在金灿灿的阳光下晒着太阳,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只有在井下生活过的人,才懂得阳光的价值。”
1985年秋天,所有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路遥决定到铜川一个偏僻的陈家山煤矿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尽管他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煤矿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要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是路遥知道,进入写作后,他就很难再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
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着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
陈家山煤矿位于铜川市西北,距铜川市大约有70公里。这个煤矿天然条件比较差,高瓦斯,地质条件也差,一个工作面控制不好,就会出现连锁反应。那里的矿工说:“在井下的工作就是用命在赌博。”
在路遥来陈家山煤矿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他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对路遥来说无用的沙发。
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当一切准备就绪,所需的就是寻找一个好的开头,这个问题却将路遥实实地困住了整整三天。待路遥冷静下来,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起点。
五六天过后,路遥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划,每天伏案十五六个小时,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写作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53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路遥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路遥心里很清楚这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他又前进了一步。路遥极力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53”这个数字,只要求自己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写作紧张起来,常常会错过了食堂的开饭时间,有时候,路遥一天就吃一顿饭。医院职工食堂的师傅与路遥对话算多的,也无非是问路遥想吃什么,师傅好给他做什么。
但矿区的生活过分简单了,不是矿上不想让他吃好,无论是陈家山煤矿领导还是医院方面,一直在尽心帮忙,只是条件有限。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有一年冬天还不得不安排飞机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没有鸡蛋,连点豆腐都很难搞到。
早饭被路遥错过了,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个矿山医院,医生职工大都回家吃饭,又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所以,伙食也相当简单。
每当路遥写作到凌晨,只能吃上一个冷硬的馒头,喝一杯咖啡填一填早已空空如也的肚子。睡下后,他时常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但一觉醒来,体力稍有恢复,路遥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用热水洗把脸,痛饮一杯咖啡,又坐在书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写作。
当年见过路遥的陈家山医院医生,如今大多已调离了这里,只有一两个人说见过路遥,回忆起当年见到的路遥,只因为知道他是大作家,都不敢上前与他搭话。在路遥工作时,更是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生怕影响了他的创作思路。
一向喜欢孤独的路遥,此刻也惧怕起了孤独。从来到陈家山煤矿,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白天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间写作间里,与他做伴的只有一只老鼠。
孤独的日子里,路遥坦言,他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空无一人,路遥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每一扇窗户里面,人们全家围坐一起聚餐,充满了安逸与欢乐。然后,窗帘一道道拉住,灯火一盏盏熄灭,一片黑暗。黑暗中,路遥不禁两眼发热。
这就是生活。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
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路遥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在这样的时候,描绘他们的悲欢离合,就如同描绘路遥自己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一个流着辛酸的或者是幸福的泪水的人,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不,这已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
有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鸣叫,这鸣叫,让路遥忍不住停下笔,陷入遐想之中。这充满激情的声音似乎是一种呼唤。路遥不由得想到是朋友或亲人从远方赶来和他相会,月台上,是他那揪心的期盼与久别重逢的惊喜。
有一天半夜,当又一声火车的鸣叫传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什么也没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门。我在料峭的寒风中走向火车站。
火车站徒有其名。这里没有客车,只有运煤车。除过山一样的煤堆和一辆没有气息的火车,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悲伤而惆怅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来这里是接某个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这虽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经错乱。我对自己说:“我原谅你。”
悄悄地,用指头抹去眼角的冰凉,然后掉过头走回自己的工作间——那里等待我的,仍然是一只老鼠。
1986年元旦在即,墙上那张表格的数字,终于被路遥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全部划掉。要出山了。要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了。要见到亲爱的女儿了。
寒风中,路遥坐在越野车的前座上离开陈家山煤矿,怀里抱着第一部已写成的20多万字初稿。透过车窗,看见外面冰天雪地,一片荒凉。当初进山时,还是满目青绿,遍地鲜花。一切都在毫无觉察中悄然消逝了,多少日子没顾得上留意大自然的变化了。坐在车上,路遥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没有遗憾,只有感叹。因为他有一份20多万字的礼物,给予这段不平常的日子,应该算是一次小小的凯旋。到达铜川市,路遥感觉自己好比进入了纽约或是华盛顿,特别是看到路边的饮食店,饼干、面包……到处都是,就想到如果陈家山煤矿有这么多好吃的,就不会那么受饿了。
张艳茜,黑龙江省绥化市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文学月刊常务副主编、陕西省米脂县政府副县长(挂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研究员。陕西省政府优秀编辑奖、柳青文学奖、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得者。出版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心中有她就属于你》,长篇小说《貂蝉》,长篇传记《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有作品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和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