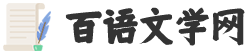原创: 姚彬彬 论衡 今天
一
我的恩师麻天祥先生今年七十岁了,先生半生坎坷,在年近不惑时,离开了在许多人看来颇有“钱途”的医生行业,转而进入了注定清寒的人文研究领域。——先生在求学阶段,一位前辈曾观其浑朴的为人气象,预料先生当“终成大器”(好像是已故甘惜分教授所说,原话一时找不到了)。事实也正是这样,数十年来,先生在中国宗教、思想哲学史等领域成就卓著,尤精佛道而旁涉百家,出入古今而成一家言,在佛学研究上,更成为同行公认的一派山斗,“圈内”凡初涉门径者,提及先生及先生的著述,无不生起几分敬意。
对我而言,与天祥师更有一些特殊的“因缘”,可以说,在我的人生转折点上,如果没有遇见吾师,很可能至今还在沾沾自喜地当一个落魄的“民科”,没准这会跟那些“隐居”的“大师”一样,正蹲在终南山上的某个角落,一本正经地刻石头呢。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点我自己的情况。——自有记忆开始,我的性格气质中已隐伏了两大弱点,即轻狂与叛逆。这样,即使自以为有不算太低的天赋,但因为这些问题,导致伏下了半生曲折的祸根。——由于家父的影响,我开蒙甚早,大约在十一二岁前后时,已经读完了所谓的“四大名著”乃至《聊斋》《草堂笔记》等书,小学期间数学也学得不错,在五六年级时候曾自学了初中全部“代数”。这样,难免面对同龄人时十分趾高气扬,祸根亦由此隐伏。
后来我有个不失深刻的人生体会,自己的精神状态一旦处于终日沾沾自喜时,难免冥冥中有股什么力量就要狠狠打击你一下(可以理解为通常说的“性格决定命运”)。我的第一次打击则来自“小升初”的考试,当时我在的小学教学并不怎么样,每年并没有几个能考上所谓“重点初中”的,但在老师们的眼里,我似乎是应该可以“板上钉钉”一定能考上的“种子选手”,不过,结果出乎我自己乃至身边所有人的预料,考试期间,许多会的题居然也都莫名其妙做错,表面看是源于“马虎”,其实后来反思,长期轻狂的精神状态,“出昏招”有必然性,就像功成名就后的聂卫平。
这次命运的挫折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这样只能“按片儿划分”,被分到一所在当时全市“有名”的挺糟糕的初中,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叹的是,初中遇见的班主任,为人颇有些“社会”,虽然也没怎么样我,但就是互相看着不爽,彼此都有很深芥蒂。——这种人在每个人的人生中可能都会遇见几位,明明你没得罪过他,他却对你具有先天敌意。——再加上我那时候很讨厌学外语,原因可能是,首先自己这方面天赋低,从来不擅长机械记忆;另外可能也是因为一直没遇见一位敬业的好老师。总而言之,在初中的阶段,结果是我的“学习成绩”开始江河日下了。
加上那几年,东北社会开始动荡,几乎全民欠薪,更有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我的家庭也不例外,虽然不算最惨,但也从八十年代的“小康”而进入了九十年代的“穷困”,经济上的困境所造成家人的焦躁状态,加上我初中阶段的学习成绩也颇让父母失望,结果是,家庭关系矛盾丛生,我自己也愈加“叛逆”。——学习成绩不好就不好吧,老子继续读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几年,大约花在课业上的精力最多也就三四分之一,倒是读了许多文史哲各种领域的典籍和学术著作,回过头看,算是“祸兮福所伏”吧。
初中毕业,我没有选择继续念高中,因为对自己的“应试”之途已经不抱信心了,对中学阶段的填鸭式教学法也感到十分厌倦,选择了读一所医药方面的中专,两年之后由中专进了大专,2002年,大专要毕业了,面临的工作选择,只能是底层劳动者,或是招摇撞骗的卖药业务员。大专阶段,是我人生最晦暗的几年,感觉天要彻底黑了。
这时,居然命运没有完全抛弃我,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机遇,有家私营的医学杂志社来我校招聘,因为我当时在校内算是“小有文名”,学校方面推荐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时间大约在2002年4月,进了杂志社后,无底薪,只有效益工资,但居然我做的不错,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日益“重用”,慢慢得到了在当时不算低的工资,这应该是我前半生“否极泰来”的第一个契机吧。
因为自己生活状态上的不如意,使我更加沉迷于大量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2002-2006年间,我收入的一少半大约都拿去买了书,不过“独学而无友”,在这方面的交流途径,只有上网,玩BBS,认识了不少爱好者乃至“民科”,在当时刚刚流行的“网易俱乐部”中,我逐渐小有名气了。
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佛学,也是开始于那几年,原因大约有三:首先,精神的苦闷,这个不必过多解释;其次,我历来喜欢读晚清民初诸大家的作品,当时的哲人们,若我最喜欢的几位,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熊十力等,“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第三,在网上跟人吵架,,这是“逆增上缘”,促使我在这方面自发地加强学习。——话说,大约在我十几岁时候,,直觉上就觉得这不是好人,满脸邪气,像一只老狐狸。
讲自己的闲话讲得太多了,会让人感到自恋,马上快进入正题了。——2003年前后,在网上认识了一位佛学方面的“民间学者”(这个词是客观陈述,并无偏见),此君年长我十岁,有独特的思想,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字,蒙他看得起,对我颇有提携,不过久而久之,他立足于当代神学和后现代哲学背景的佛学理解,给我造成了许多疑惑,而且难以认同,这时偶然在书店中买回一本书,即麻天祥先生的《境外谈佛》,一读之下,拍案叫绝,我的许多困惑一下子烟消云散。——先生立足于晚清民初诸先贤的学术思想解读,恰恰是我熟悉而乐于接受的,而且,先生在西学上取法于康德、黑格尔诸家,这也是我十分服膺的(尤其对黑格尔亲切),所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我耳中更如霹雳惊雷,有种“找到组织”的赶脚,觉得这才应该是我努力的方向。
于是乎,大约在2004年下半年,不揣冒昧,给先生写了封介绍自己情况的信,表达了渴慕之忱,并附上了两篇自己发表的佛学习作(其中一篇是在网上认识的那位先生的帮助下发表的),不久之后,居然得到了先生热情而不惜溢美的回信。——后来我想,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先生为人宽厚,此外大约我当时的“医学”身份,也会让先生觉得有几分亲切吧。
2005年上半年,我利用一次单位出差的机会,转道武汉去拜访先生,竟蒙平日深居简出的先生亲自来火车站接站,并住先生家中多日,得到先生进一步的亲切教益和鼓励。——后来回忆,当年我在先生面前的表现,乃至所讲的一些话,实在还是够轻狂的,偶尔忆及深感汗颜。但先生竟不以为忤,鼓励我等待合适的机会来报考他的研究生,先生说,按我当时的程度,如果不走专业的学术道路,难免有些可惜,先生的话,促使我进一步下了决心。——到了2005年下半年,我所在的杂志社出现重大变故,我一咬牙,干脆辞了职,回到独居的家里“闭关”复习考研。
2006年,先生在武汉大学发起筹办“佛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者皆国内大牛,而当时我的学历还是大专,先生居然邀我作为“正式代表”参会,这对先生显然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对我更属于“异数”,好在在会议上的表现,貌似并未给先生丢人。
后面的事情,我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后记中有交代,偷懒引述如下:
接下来的数年,决心恶补自己一直缺失、几乎是零起点的外语(日语),为此花费了我绝大多数的时间,却因这方面天资太劣,所得无几,两三年后,才勉强可以对付一般的考试。2007年,终于鼓起勇气,报考了麻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但分数线出来后,还是以5分之差栽在了外语上,虽然先生多方设法,当年终无缘于门下,遂经先生的推荐,远赴黔州,投于已故任继愈老先生之嫡传宋立道先生门下,也算无幸中的万幸,终于否极泰来了。
……
2010年报考博士,多年的夙愿终于得偿,来到珞珈山,投入麻天祥先生门下。——之前的数年间,也一直受到麻老师的提点,他想方设法为我的学术前途创造条件。就读博士以后,先生的教导、勉励,随时鞭策我不断前进。先生洞察我有几分狂傲和自命不凡的习气,时加警醒、点拨,以期我能有更大进步。在武大的这些年,无论出版著作,还是发表论文,多经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先生还经常携我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引介于国内同行。先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如果我今后在学术上能够小有所成,无疑当多拜先生所造就。
——年过三十以后,我的两大性格弱点,也就是“轻狂”与“叛逆”,后面的两个字其实没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懂得收敛了;前面的两个字“轻狂”,自我反思,“狂”字依旧,但“轻”字确实慢慢去掉了许多,这其实主要来源于先生多年来对我“因病与药”的磨砺之功,终生受用不尽。
二
上面讲了天祥师对我的知遇之恩,下面讲先生学术思想对我的启示。
抛开具体的一些问题不论,单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三端:
首先,是先生反复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先生早年出于侯外庐学派的传人张岂之先生之门,以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平生学术根基,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则是“侯派”一脉相承的不二心法,其说至少可上溯至黑格尔。这也是我在人文学术上最为认同的基本立场。因为,在处理任何具体的人文学术问题时,若忽略历史观念,不考量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若哲人、思想家,乃至文学家艺术家等)的社会环境景与平时际遇的影响,就文本而言文本,总是免不了纯任主观而过度诠释,追求可能本来子虚乌有的“微言大义”,陷入自说自话的文字游戏;反之,任何历史上的重要文化人物,他们的平生学说思想,总是有其前承,他们要回答前辈留下的一些问题,也有“接着讲”的后来者,任何一种学说,形成之后,自有一种“内在理路”蕴含其中,学说最终会走向何方,往往早已蕴含在其早期已存在的某些自身悖论之中。天祥师常常引用汤用彤先生的话教导我们,如“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等论,我个人的理解,这种“心性之体会”便是深入到某种思想学说中的内在逻辑径路,才能考源抉流而有所发现,也不至于迷失在一家一派的具体观点当中。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的操作其实很难,我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曾感叹当下“很多文科人士,无论搞中学还是搞西学的,研究谁就往死了夸谁,对于所谓‘时代性’或‘局限性’,完全不管不顾,觉得‘真理’就在于兹,从文本中进去了,却出不来。前代大家们的那种高屋建瓴挥洒古今的风采,已很少得见了。”——我觉得,吾师的佛学研究乃至宗教研究,继承了先辈汤用彤、胡适、任继愈诸先生的基本研究范式而进一步有所发明,至始至终拥有卓越的“大局观”,每发一义,切理餍心,最为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
其次,即先生所开创的,对于古今佛学义理体系为“非本体的本体论”之总体把握。“非本体的本体论”概念之提出,源于麻老师2001年发表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顶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中的论文《中国佛学非本体的本体诠释》,后来在他的许多论著中都继有阐发,我认为,这是先生平生对佛学义理的“元问题”研究的最重要贡献之一(甚至没有之一)。
许多古今中外的佛学家认为,是不承认有所谓“本体”的,因为的“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的,解构了“本体”的存在。但是,这种解释一向不能让我全然心服,因为纵观古今哲学思想,对于现象世界的立场,无外两种,或以为真,或以为假,以为“真”者,往往会探索隐含在万物背后的“规律”或“理则”,乃至探索万物生成的终极根源,就像中国道家和儒家所谈的“道”;以为假,或不完满者,则往往会追求祛除假象而呈现真实,如柏拉图所追求的“理念”(idea或eidos)世界。——按我的看法,无论是“道”或“理念”等,都有一定的“本体”性质(虽然这种意义上的“本体”比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Ontology可能要宽泛)。故近人章太炎先生说,凡古今“言哲学创宗教者,无不建立一物以为本体。”(《建立宗教论》),对此观点我基本认同。——虽以森罗万象为无明所造,但真的没有对“真实世界”探索吗?恐怕未必尽然,熊十力先生认为唯识学中的“种子”“真如”皆有本体性质,虽然遭到大多数佛学家的反对,但其说并不能说毫无道理。至于“真常唯心论”中印度的“如来藏缘起”,中国《大乘起信论》中的“真如生万法”,不是本体是什么?——退一步说,就算承认早期无本体观念,何以后世又从中生发出了类似“本体论”的思想?
这些难题,曾萦绕我心中数年之久,后读到天祥师的“非本体的本体论”之说,则顿时拍案叫绝!先生的思路,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早期的“非本体”中亦隐含着对“觉悟”的追求探索,这种“非本体”本身就有本体性质,若佛家所谓“实相非相”,实则“非相”亦实相。“非本体的本体”向前发展,自然会衍生出描述终极真实的“空性”、“真如”、“佛性”、“如来藏”的“心性本体”。先生后来在《道生的佛性论及其对中国心性哲学的建设》(2009年)对这一思想有更为凝练的论述,文谓:
佛(Buddha)称觉悟,有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的不同阶级,觉显然是佛家的终极追求。觉,就是要觉悟大千世界、诸法万象,一切皆幻,其根本就在于缘生,而不在于“本生”或者说创生。这是哲学的显著特点,也是佛学区别于其他本体论哲学的本质精神。然而,觉的主体是人,觉的载体是心性,换句话说,觉是人性之觉,觉性就是佛性,佛性就是心性。如是,觉的主体、载体和觉的内涵,也就逻辑的联系在一起,原来对“觉”的追求,顺理成章而为对“心性”的诠释和印证;缘起性空的辩证思维,摇身一变而为真常唯心的心性本体论。
此说窃以为当系先生多年来“心教交参,千锤百炼”之所得,细玩其义,许多义理上的两难问题都可涣然冰释,断不可轻忽视之。
第三,关于禅宗为“大众化的庄老哲学”之说。这是先生代表作之一《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中的核心思想。——关于中国禅宗(惠能以后)思想受到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深刻影响,虽前辈学者若胡适、印顺、张中行等早有论及,但在这一观念下系统梳理整个的禅宗思想发展史,则为吾师所首创,而且先生从“禅”的词源问题上入手,认定“中国禅”的观念一开始便呈现出了《庄子》哲学的影子,解决了一个前辈学者没有注意到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思路下,天祥师对整个中国的理解,都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总体而言,他是从中国本土思想哲学的逻辑进路去对中国佛学(或说“中国化”)进行理解和诠释,这虽然是前辈汤用彤、任继愈诸先生早已开创的一条思路,今人之承继者却显得寥寥无几。——近十多年,当代中国佛学的研究也渐渐受到了欧美重梵、巴、藏文的影响,虽然未必是坏事,但坏就坏在整体的跟风,乃至于今时甚至有人写个惠能思想,也会拽几个梵文词汇,这显然就有些滑稽了。
中国文献,整体上以大乘为主(确切说以大乘中、前期为主),早期的译本来源,多为西域流行的“胡本”(以西域文字写成),隋唐以后“梵本”才多了起来。——但问题是,现存汉译文献的“梵本”,绝大多数早已烟消云散,今人往往依据几页来源不明的残篇断章进行研究,其真伪姑且不论,问题在,印度文献来源多端,不同学派往往文字大有出入,而且往往多靠口头传承,你看到的这几页,何以就能肯定那就是古人所看到的同一版本?若据此便声言古人“错误”或“误译”,恐难免厚诬古人罢。
汉语文献,浩如烟海而自成体系,并不是说梵巴文字的研究不重要,而是未必那么重要。——吾师就本土思想源流(当然绝不是忽略印度、西域的渊源)而诠释中国佛学要义,或有人认为有些“矫枉过正”,然其苦心孤诣,实在此也。
三
2013年我博士毕业后,自然面临找工作的紧迫问题,这又是一个“老大难”,因为,现在绝大多数高校用人,都讲究“第一学历”,这个我当然不合格,天祥师想尽办法,最后把我推荐到他的母校西北大学,蒙该校诸先生的关照,基本上算是谈妥了。——不过在博士论文答辩后,听到当时的答辩委员之一,后来我的师兄聂长顺教授说,有一个留校在著名文化史研究泰斗冯天瑜先生处继续做博后的机会,于是天祥师又通过长顺师兄向冯师引荐了我,并亲自给冯师打了电话,几经波折,在2013年底进站工作。
2005-2015年这十年间,算是我人生的转折阶段(同门好友黄敏戏称,我这些年是一部典型的“民科逆袭史”),之所以最后算是实现了“初心”,主要是小子何幸,竟遇恩师麻天祥、宋立道、冯天瑜三先生(以结识的先后为序),关于宋立道老师对我的深恩,日后再为文述之。——吾师冯天瑜先生之学浩博无涯,入其门下之后,不仅进一步开阔了学术视野,领略到我过去未尝想见的境界;就现实上的问题而言,若无冯先生以高龄之身,百般设法,多方奔走,以期突破制度性瓶颈,我最终能在博士后出站后(2015年12月)留在武汉大学这种所谓的“重点高校”工作,显然是天方夜谭一样的事。
2008年,吾师麻天祥先生逢六秩寿庆时,余尚未正式忝列门墙,遥寄二首小诗聊表寸心:
其一
少壮有奇志,俯仰尝问天。
不忍众生苦,悬壶济世间。
返身明大道,贝叶探幽玄。
行脚遍五洲,法音动大千!
其二
风骨宗魏晋,悲心契近贤。
禅道明不二,行化六十年。
吾愧为宰我,仰高钻弥坚。
惟具香一瓣,颂师福寿延!
今年,先生欣逢古稀,学生感慨万千,兹以所撰寿联附文之末,并馨香祷祝先生长寿,联曰:
先生今七旬,起于杏林兴于杏坛,道通身心性命,法音播扬四海;
著述传百代,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兼中西古今,声教遍布五洲。
于2018年5月30日,学生彬彬敬撰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