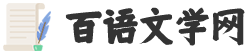先生素描(四)
——学界文评“双星”
(上)
丁帆近照
作者简介:丁帆,学者。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1979年以来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百余篇,有《中国乡土小说史》等著作三十余种。
曾华鹏
镜头1:讲台上,他手捏着粉笔,用略带鼻音的浑厚而极富磁性的中音和十分投入的情感,生动地讲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
镜头2:他半倚在那个已经磨得发亮的藤椅上,时常用右手托住下巴,食指与中指分开在脸颊上摩挲着,与人交谈,风度谦谦,有时颔首微笑,有时嬉笑怒骂,声音有时低徊,有时高亢。
镜头3:高旻寺,在破败的康乾行宫前,在修葺的雄伟塔寺和佛像前,他的朗朗笑声划破了寂寥的长空。
镜头4:病榻上,平静地交谈;临别时,紧紧握住的双手,道出的是永诀时的千言万语。
范伯群
镜头1:瘦西湖畔,他幽默风趣的言谈和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每一个人,他的处事风格也是别有情趣。
镜头2:在宜兴饭桌上,他劝食比劝酒还要得体,尊老爱幼,感动着教材组的每一个人。
镜头3:在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重建50周年暨文学系创建108周年”庆典会上,他激动的颤音。
镜头4:在“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组稿会上,他佝偻的身影。
镜头5:病榻上,他戴着氧气罩,已经不能言语,只是用眼神说话;诀别握手时,握力却比往常大了几倍。
一个沉稳深沉;一个开朗儒雅。这对文坛双星雕像的音容笑貌永远镌刻在许许多多的学者的脑海之中。
曾华鹏先生与范伯群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51年入学的同班同学,曾华鹏是班长,范伯群是系学生会主席。他们师从贾植芳,二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论文合作,他们的友谊与合作延续了一辈子,堪称学界的一对终生的“双打选手”,是永不凋落的学界“双星”。
那时同班的同学当中除了曾华鹏、范伯群外,还有两个大才子,那就是早逝的施昌东和后去的章培恒先生(下次我得专门书写这一个最具个性的学者)。施昌东1970年代末改攻文学理论专业,而本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章培恒先生却改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了,他们二人在各自的专业中成就斐然,可见只要有才华,放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他们各自设计出了毕业论文作家论的主攻方向,曾华鹏写《郁达夫论》,范伯群写《王鲁彦论》,施昌东写《朱自清论》。曾华鹏出手快,《郁达夫论》首先完成,尔后范伯群也参与了修改,竟然在贾植芳先生刚刚被打成“胡风分子”不久时,就在《人民文学》1957年五、六期合刊上发表出来了。那是《人民文学》破天荒第一次辟出专栏发表文学评论文章,而且是两个不知名年轻作者的文章。秦兆阳在《人民文学》“编后记”中说:“作家论是我们盼望很久的,郁达夫又是‘五四’以后,有独创风格,有广大社会影响的重要作家。文中对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是有独到见解的。我们愿以发表‘郁达夫论’作为一个开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对我国现代以及当前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大概是《人民文学》杂志发表长篇作家论空前绝后的编辑史了。那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事情啊,全国许许多多学人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都是惊叹不已。许多年后,我在扬州师院图书馆里看到这本杂志时,那种激动是无法形容的,感到无比的荣幸,因为先生就在我的身边。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当王富仁和许子东读到这篇50年代的作家论时,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无疑,这是文学史回避不了的一篇宏文。
可是,正是贾先生因胡风案的被捕,让他的弟子们也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用范伯群先生的话说,他们是贾植芳先生的得意门生,那么也就被甄别为“几个小分子”了。毕业分配,本来是留校的曾华鹏和范伯群也都被发配到苏北,前者先是被分在扬州财经学校,1958年苏北师专成立后,才被调入现在扬州大学和以前扬州师院的前身—苏北师专。后者被分配到南通中学,他从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坐了一个五等舱艰难地抵达了南通的天生港。
他们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两人在毕业分手时的特殊的告别仪式在那个时代却是殊异的行为举止。两个年轻的“胡风分子”在悲情浪漫的情绪里做了四件事:“第一,到国际饭店体验、享受一下西餐;第二,到先施公司去看一看那里的雕塑;第三,看一场电影;第四,来一个合影。这个仪式的核心内容是,两人当时相约,以后一定要相互扶持,回到心爱的文艺岗位,不能就此埋没一生。他们拍的合影照片,后来曾华鹏说是‘两只惊弓之鸟’。这张照片范伯群一直留在身边,纪念着两个人一生搀扶前进的誓约。”(摘自陈霖的长篇访谈录《保住智慧的元气》)这是那个时代大学生“最浪漫的事”了,而我猜想,他们更多的还是怀才不遇的悲伤,学术抱负不能施展,也只能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水仰天长啸生不逢时矣。
正是由于戴着摘帽“胡风分子”的原罪,他们来到了江苏的苏北地区,把自己的大半生交付予这片贫瘠的学术土地,从个人的学术经历来说,这固然是遏制他们学术发展的悲剧,用范伯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超度知识分子的原罪中浪掷了青春。”(范伯群:《“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然而,从对江苏的学术贡献来说,正是他们的到来,为苏北这片未被开垦的中国现代文学处女地播下了学术的种子。作为拓荒者,他们在几十年的辛勤耕耘中,不仅个人在学术领域卓有建树,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一支支强大的学术团队,屹立于文坛学界,这无疑又是江苏学界之大幸。
曾华鹏
曾华鹏先生是我在扬州师院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那时他是我们的偶像,听他的课乃是一种享受,我曾经在另一篇随笔中描述过那种场景,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正因为有曾华鹏先生的存在,扬州师院的学术氛围和气场才有,学术领域和特色才存,学术团队和梯队才在。前些日子,有一位中文系的老教师看了我写扬州师院中文系先生们的素描后打电话给我,最后反思诘问:为什么一批优秀的学生没有能够留在扬州大学呢?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良久,除了走出去才有更大的学术空间的因素外,更多的原因还是一个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学者的学术气度问题,因为曾先生从来就不会强留自己的学生在自己身边。在我与曾华鹏先生的接触中,许多次的聊天,他都吐露出这样的观点:学生不是老师的私有财产,也不是一个学校的校产,只要能够发挥个人最大的学术能量,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是的,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老师最值得欣慰的事情,其空间的转移则是无足轻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华鹏先生的眼光和心胸是辽远阔达的,他无形之中是在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输送学术人才。扬州师院能够为此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即使自身的学科有所萎缩,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站在急功近利的学科排名的立场上去看问题,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培养基础人才的最好的学校之一,有此足矣。由此,我看到的不仅是先生的淡泊,更是他长远的明志胸怀。
1955年因那个胡风案,曾华鹏先生个人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生活的道路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先生却没有“沉沦”,正如他的同乡、同学和终身的挚友潘旭澜先生在其散文随笔《五十年之约》中所言:“半个世纪里,华鹏的遭遇起伏最大。他本是班长、学习模范,谁知临近毕业被‘反胡风’卷了进去,成了贱民。幸而他并不绝望,不颓唐。但从此谨言慎行,以求平安无事。凭着没有被改造净尽的才华和加倍的勤奋,从‘控制使用’的中专教员,熬成大学教授,系主任,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著作丰硕的学者,并因此而被推举或指定为什么代表和委员。他研究郁达夫、冰心、鲁迅小说和《野草》、‘九叶’诗派的诸多论著,我都在油墨未干时就读了。由衷赞佩之余,也不能不感到时代与环境的制约。好在他能极力寻求丰腴而又制约较少的地带,不断地开拓突破。从而,他的学术成就受到老中青同行的推崇。以他的造诣加上情理并茂的口才,他讲课广受学生称道,不少人听得入迷上瘾,因此确定或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我以为潘先生的这一概括真是十分精准的。
先生的学问与才华自不必说,从他1957年首次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关于论郁达夫的洋洋洒洒四万字的长篇论文中就可见一斑。在这里,我只想截取几个镜头,来勾勒出先生的性格与品格。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华鹏先生的课多是在梯形大教室里上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有时是盛况空前。先生上课时,无论板书与否,都喜欢捏住一支粉笔,有时是正常的拿捏,有时却是中指与食指夹住的抽烟状,后来问之,果然,原来他也曾经抽过烟。我想,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能够消愁之物,除了酒,就是烟了罢,这种夹烟的习惯是下意识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标记。
先生上课讲求张弛有致和起伏变化的节奏,课堂上不时传出学生们的笑声和掌声。他的声音略带鼻音和福建腔,浑厚而洪亮,极富磁性,且是那种从低音到中音的渐变,偶发高音,那必定是到了十分激动之时,再从高音到中音,也偶有到低音的过程,颇有抑扬顿挫之节奏感和轻重缓急的旋律感,随着讲析的内容和不断变幻的情绪而起伏。我猜想,先生是把上课作为一门艺术表演来备课的吧,所以,学生们也是将它作为一种艺术的享受和思想的洗礼来聆听与回味的,它是绕梁终生的,难怪“趋之若鹜”者众呢。一个教师能够把一堂课上成一曲长长的、旋律变幻无穷的、章节与节奏十分清晰的“钢琴课”,那是需要何等的工力和功夫啊。譬如他在分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用梵婀玲的音乐旋律和效果来形容作品的节奏;在分析《药》时,把乌鸦的叫声与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风景勾连起来……从而把一部部鲁迅作品的精华谱成一首首交响诗,将鲁迅的写作心境和曲笔都生动地表现抒发出来了,让人看到了另外一种诗画音乐般的人生艺术境界,这就是在作品的基础上对生活和艺术现实的再创作的过程,没有高超的艺术工力是难以完成的。于是,在听众眼中,他那手中的粉笔似乎变成了长长的指挥棒,把一曲交响乐推向了高潮。他那由低到高,由高到低的音符,让人完全进入了作品的情境之中,随着旋律而忘情忘我,让本来读起来平淡无奇的课文,在他的讲析中成为一曲不朽的交响诗,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多少年后,当我和朋友们谈起先生的授课时,将他手中的那支粉笔说成是大师手中的“艺术魔棒”。
与先生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倘若是不熟悉的人,他会表现出一种慎言的态度,只是倾听来者的叙述,很少说话,不断颔首微笑。然而,一俟遇上熟络的朋友和学生,就会呼茶畅谈,谈兴骤起时,甚至会开怀大笑,那略带鼻音的浑厚嗓音,往往会感染着你进入一种无拘无束的交谈语境之中。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有一次我们去他家,那天他十分兴奋,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复旦大学的老同学老同乡潘旭澜先生给他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内容是从小道消息到国家大事。嘴上虽然怪罪潘先生太能侃了,抓住话筒不放,心里却是美滋滋的。人们都说先生是一个谨语慎言的人,其实,、有良知的学者。
不能忘却的镜头是,在先生家聊天,他让师母给我们沏上一杯茶,自己却是用那只大玻璃壶泡的决明子当茶喝,因为他说自己的眼睛不好,只能以此代茶了。他半倚在那把坐了许多年的幽暗发亮的藤椅上,翘着二郎腿,有时严肃,有时微笑的影像,在我脑海当中成为了永恒的定格。可惜当年没有想到带上一架照相机,如果将这个镜头拍摄下来,挂在我的书房里,那便是最好的永久纪念。
犹记得当年我们一行四五人随先生去瓜州的高旻寺一游的情形,,打招呼去游览尚未完全修复的天下名刹。站在破败不堪的康熙和乾隆的行宫前,先生发了幽古之情,同时,也慨叹人生之寂寥。那个住持方丈是有名的德林长老(1915 ~ 2015),法名妙悟,字悟参,号德林,河北丰润人,原名为梁怀德。他用三十年的时间重建高旻寺,其设计的大禅堂被称为“中国第一禅堂”,是一个颇有现代意识的佛家人士,其建筑的恢复全是此公倾全力而建造的,“扶刹竿于既倒,兴伽蓝于废墟”。先生说高旻寺就相当于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院,是中国的最高研究机构之一,先生表情严肃地告诉我们,时任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艾煊不久前来此挂单过。那次的游览,却让我对先生的复杂心境难以猜度了,先生若有所思,若有所参,若有所悟的神情让我浮想联翩,难道先生真的相信有天国存在吗?
先生无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也有流泪之时,一次是听说,两次是亲眼所见。从中可以见出其心底里深藏着的人性柔软的一面,虽然常人是难以见到的。
那次他的爱徒李华岚不幸英年早逝,据说他听到这个才华横溢的散文作家去世的噩耗时流泪了。李华岚在病中时,他还专门为其散文集撰写了评论发表,可见他对学生的宠爱是深藏不露的,虽然他平时不说,但是留在心底里的呵护却是最动人的。
在叶子铭先生弥留之际,曾华鹏先生特地让张王飞和我陪同他前往医院看望,那天,他风尘仆仆从扬州赶来,一进病房就用福建泉州家乡话抽泣地呼唤着:子铭!子铭!!子铭!!!(写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先生当时几乎哭出声来,我和王飞背过身流泪,不忍目睹。那时的叶子铭基本上已无知觉,也许是乡音,也许是友情,靠鼻饲闭目无语的叶子铭先生居然流下来两行清泪……出了病房,三人一直无语,待到分手时刻,王飞才不无深情地说了一句:曾老师,你也要多保重啊!他的这句话便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于是,在我后来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尽快地将先生的成名之作《郁达夫评传》赶出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在做出大幅度修改增删时,还是用较为原始的撰稿方式,在打印稿上,用红笔一字一句地写满了增删的内容,字斟句酌的严谨文风,让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羞赧汗颜。作为给先生80寿辰的献礼,当那本书以精美大气的装帧呈现在先生面前的时候,先生摩挲着这本凝聚着其毕生学术沉浮的大著,笑了。
2017年初,我们启动了“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曾华鹏先生卷由他的学生张王飞编纂。王飞说,他是收集了先生所有的文献资料,含着泪水编完这本著作的,可惜的是,先生没有亲眼看到这本凝聚着他毕生论文精华的大著面世,但我们是将这本著作当作祭奠先生的最好礼物予以供奉的。
先生病了,我和王飞相约去扬州探望,那虽然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但是我俩的心情却是阴沉的。走进病房,他让人摇起病床与我们交谈,看起来精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待到临别之际,他直起身子与我们握别,眼里分明噙着泪花,我们欲泪,便匆匆逃也似的离开病房,偷偷在走廊中拭泪。
在先生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的老老少少都伫立了半个多小时,足见先生的人望之高。作为近半个世纪的老同学和合作者的范伯群先生在所有的悼念者中是最悲痛的老者了。
本文刊于《雨花》2018年第4期
《雨花》2018年第4期目录
丁帆专栏·山高水长
先生素描(四)
——学界文评“双星” /丁 帆
短篇小说
偶遇/徐立峰
亲爱的小孩/诗 篱
跑马黄/华津谷
汗手/周 伟
是谁偷了我的珍珠项链/张荣超
文学苏军
大地公民/张羊羊
平等地与世间万物对话
——读张羊羊散文《大地公民》/李晓伟
散文现场
睡眠唯美/傅 菲
人在岸上 /张吉安
我要给名声写封信/雍 措
自然物语/朱 雪
阳光不拐弯/冯六一
鹤隐山房记/叶小龙
文学评弹
“对神圣之物的洞察”:米沃什访谈
/切斯瓦夫·米沃什 辛西娅·L·赫文
李以亮译
雨花·艺术
葛震作品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