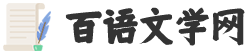父亲,生于乡下,初一缀学,16岁用自学的中医治病,25岁一举考入中医大学,苦学六年半,直至病卧都在治病救人,叹天怒英才,73岁离去。终生致力中医研究,济人无数,素有神仙之称,博学敏思。父亲于1962年之毕业论文在今日看来仍然有极高的水准,引经据典,将中医之医理,如出家珍一般娓娓道来。
-------------------------------------------------------------------
漫谈辨证论治与理法方药
略论“辨证施治”的实际体现——理法方药的建立及其临床意义
理、法、方、药是中医对于每个疾病在“辨证论治”的原则下,通过 四诊、八纲及其他辨证方法,从具体病人身上,所完成的一套治疗体系。这个体系既是“辨证论治”的实际体现,又是医生给于每个病症的诊断与治疗的准确概括。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医对处理一个疾病全过程的基本结束。因此,能够系统地了解它的产生根源和建立过程,以及临床上的实践意义,对于每个中医的治疗工作的顺利完成无疑是有很大的帮助。《内经》所提的“治病必求于本”,这虽为医家之大宗,辨证的先河。但如从整个医疗过程来看,去求“本”、求到“本”,也是为的给理方法药找求建立依据。后面还要实际的完成理法方药才能结束全部过程。所以,张景岳也说:“以凡治病者,必须先探病本, 然后用药”。这“然后”二字显然就包含着下面还有一系列的关于理法方药的形成问题。因此,鉴于理法方药的建立,不仅是中医治病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也是 医疗效果的直接依靠。但是,仅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的人过份去强调找求病本的“辨证”;而忽略理法方药建成的“论治”。如常听人说:“治病容易,识病难”,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像喻嘉言这样的人也是说:“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证。”似乎只要辨证辨得好就够了,其他都可以一挥而就,用不着操心。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有很大程度的片面性。因为,辨证与论治联合起 来共同概括了中医医疗工作的全部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所以,无论忽视或放松那一部分的困难性,都会举足轻重,影响至大。谁都知道,良好的医疗效果,不仅要靠正确的辨证工作为前提;而且,也有赖于正确的施治方案 作后盾。有多少的优秀临床家,他们就是不仅是把辨证与论治放在同等地位;而且,连其他的细节部份也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如李士材就说:“病不辨则无以法,治不辨则无以痊”。沈括也说:“治病有五难:辨疾、治疾、饮药、处方、别药。”这些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老前辈,就是以切身的体会告诉我们治疗工作上的艰巨性,不能忽视那一个方面。
再说:理法方药的制定,完全是来之于病人,既反映了疾病的具体特征,也代表了病人的实际要求。即是说,不光是从病人身上来就完了,还必须要回到病人的身上去,最终的目的是为他解决问题,把病诒好。这当中,显然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问题。就是实践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考验医生的过程,工作做得怎么样?可以全见分晓。“辨证论治”只是一项原则,要做实际工作,那就只有靠理法方药才能完成。由此看来,巳 无须多说, 理法方药的实际意义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设想:辨证辨得极其准确,寒热分明、表里清楚......。可是,理法方药不够健全,尤其是方和药对不上头,能回到病人身上去吗?当然,“粗工凶凶”可以强加上去,但后果一定不堪设想。个人对于理法方药学得较差,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探索,仅仅是一些肤浅的和支离片断的体会,错误定然很多,缺点更难免,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谨守“辨证论治”的原则为理法方药寻求理论根据。“辨证论治”这一原则,是中医治疗学上的最高准则,也是中医的治疗 特 点和精华部份。多少年来的实践证明,巳经为每个中医所必须严格遵循的道路。不过,问题的重要性还不在于是否大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而在于走得怎么样?如何地走法?《列子传》上有段故事发人深思:列子学射箭,并且很快即能射中,他高兴得很。但是,去告诉老师关尹子时,关尹子要他回答射中的道理,他就不行了。后来又苦苦学了三年。我们治病的人很多,而且,确实也治好不少的病。但老是像列子开初那样,说不出治病的道理来,也是不行的。因为,讲不出道理,就不能把握住规律,就不能保得住治一百个,一百个都正确。只有把规律掌握了,临证治病时,才能知道那是对的,那是错的。对的巩固,错的纠正,日新月异,逐步提高,永远走着正确的道路。为什么要这样呢?许多人能治病,而且治好了病,这仅仅是一种现象上的问题,是人们感觉到的东西罢了。要进一步知道,为什么能治好病?怎样治好的病?那才算得是本质上的问题。本质上的问题,不是感觉所能解决的,要用理论才能回答。因此,我们要想:既能治好病,又要讲得出道理来。就必须要把感性的知识上升到理性的知识,才能办得到。的情况共同来说明疾病本质的阶段性。一 切事物不能离开它的环 境而孤立地存在,一定和周围世界取得密切联系。客观事物的历史性、常是影响事物显现阶段性的 普 遍情况。疾病也是这样,它是不断受 着内外因 素的 影 响,而处于一个变 动的过程。我们巳经认识到,辨证的内容中,不仅是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从形形色色、瞬息万变的证形去找到它的一般个性的本质特点;同时,还要知道它所在的阶段性上的具体特点。因此,就必须把一般的个性和显现阶段性上的具体性区别开来。要是认不清疾病 发展阶段性上的具体性。也就辨不出疾病本质在不同阶段时期的具体性。因而也就会放过疾病现象中最本质的,最富于时间性的特征。这种情况,在《伤寒论》上是表现得最明显不过的。论中的六经,就是把疾病本质最富于时间特征的具体特点,给予不同阶段的最大概括。太阳病,就是概括了《伤寒论》太阳病这个阶段范围的疾病性质。是伤寒初期病变部位及其特有征象的最本质的显露时间。故曰:“伤寒一日,太阳受之。” 总的说来,病是要变的,不变的病是没有的。既然要变,就不能不反映它的时间特点,忽略了这一特点,就不能把握住病证的变化规律。老是跟在疾病的后面跑,不仅徒劳,而且每每失却大好时机,延误病情。《伤寒论》97条:“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在这里医生就是凭“渴”这一特点,可以前进一大步,跨入阳明阶段,于病迎头痛击。204条:“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在这里医生又是凭“呕”这一特点,不致犯冒进,谨守少阳阶段采取就地正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一个辨证的过程,就是许许多多抓特点的过程,既抓共同的特点,又抓不同的特点,还要抓变化的特点。这就是辩证法的基本精神。
以上所述,只作为辨证问题上的一些思维方法,很不全面,可能还会有错。为有助于辩证,才在这里首先提出。因为,大概的医生,在临证时都往往急于求成,忙在开方、想药的时候居多,正如看书的人都忙于看内容,对凡例是很少问津的,这无疑是会影响效率的。
二、准确运用四诊的汇集资料方法深入细致地把病人有关病情资料汇集起来为建立理法方药准备基础。四诊作为祖国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方法,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纪时代就有了记载。如《周礼·天官》上说:“医师究人之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察天五运,并时六气,诊人五色、五声,九窍九脏之动,以探百病,决死生之分。”公元前五世纪的秦越人入虢之诊,望齐候之色,更出色的运用了切脉和望诊。公元前三世纪,中医的第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以望、闻、问、切四诊作为诊断疾病的方法的理论基础。汉末张仲景,在《内经》的基础上,更创造性的发展了四诊的具体运用。著出了第一批辩证论治、理法方药齐全的专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自此以后,中医学便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发展为世界医学独特的组成部分。
四诊是四种诊断疾病的法法,它的对象主要是针对病情,但最终目的仍然转归成证,这一点与辨证的对象是相同的。因此,在四诊之前,为了提高准确性,对证的概念是必须首先了解的。否则,不仅辨证时无所辨,连进行四诊也会失掉方向。但是又由于证是从病人身上概括的东西。因此,具体说来,四诊的对象就是病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医疗不是治病,……是治疗病人本身(莫得洛夫)”。
中医学上的证范围极其广泛。这个问题许多人早已讨论过了,大同小异,都认为它是概括着一个患病人多方面的临床体征。除了狭隘的“症”的显示而外,就是联系一切病情的表现,如发病原因、脏腑经络关系、病理机转、生理状态以及疗效观察等等程序应有尽有的综合反映。总而言之,一切疾病的现象,都可以概括进去,综合成“证”的概念。仅仅在于实际的具体要求之下,为了实用,才将它划分成各式各样、若干数目的类型,如某某病证某某汤证等。这里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医要这样,常言“证”而少言“症”;多辨“证”而略辨“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只能从中医学的角度,即中医本身的特点和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关系上去理解。因为,单言“症”,未免太局限、太狭隘,既不足以概括庞杂病情,也往往束缚方药的施展。更不适合辨证的综合观点。而辨病呢?又常为力所不及,很难求得“见病知源”。因此较理想而实用的方法就只得借助于“证”这一概念。证者,凭据也,有凭有据方谓之证。病有病的证;方有方的证;经有经的证;络有络的证;脏有脏的证;腑有的证;无处不见证,也就无处不言证,无处不辨证。由此可见,证是中医工作的核心。没有证则一系列的工作,将涣然失散,无所适从。但这些证怎样来的呢?靠四诊吗?然而四诊所收集的仅是些分散的和单个的“症”。同时,病人也不会一个一个的反映出完整的“证”。究竟证是那里来的?这就由医生的分析与综合了。医生的对证综合过程,既有别于四诊也不全属辨证,而是四诊的继续和辨证的开始。
为了进一步明确证的概念,这里不妨再就“柴胡证”为例来谈谈关于什么叫柴胡证,有人把“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作为它的定义。其实这里究竟指的是那一证,又是多少证中之一证?尽是些猜想的结果。如果要客观点地说,只能笼统认为:柴胡证就是指实用于柴胡汤这个方药下的许多病情的集中。《伤寒论》里面的柴胡汤证就是泛指的基本上属于小柴胡汤适应的多种症群。为避免庞杂,在此仅就几处醒目的提要略加说明。不过,方向是不受限制的,凡是能用上小柴胡汤证的病情,都能概括入柴胡证。论中正式标明用小柴胡汤的条文相当多,大概除桂枝汤外,没有哪个汤可和它相比。因此,柴胡证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泛。但也不是漫无边际。应该注意不要把少阳证也压缩在内。那样就真的够大 了。前已述及“证”不是孤独的一种或几种症状的表现,是联合许多疾病现显及其内在联系 的综合反映。柴胡证当然毫无例外。这里就是为了证实这种情况,便于为四诊、八纲打下础基,便于最后确立理法方药。《伤寒论》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肋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更,或心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本条是公认的对柴胡证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一条,其中几乎全部指的临床症状,但如果一概以搜罗症状来归纳柴胡证,那么,后面的许多条内就不太适用了。97 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此条就是把病因与病理机转、及脏腑关系,效果转归皆联系起来,使人清晰了解柴胡证之来龙去脉。因此,这也是简单证状观点所不能解决的问题。100条:“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此条柴胡证是试出来的,症状起不了决定作用。99条:“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此条扩大了柴胡证圈子,引进了太阳,阳明的一些症状,单一凭症状当然说不通。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结,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本条病情,已够复杂,由太阳一直到少阴,所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齐全,但辨证之下,仍不离柴胡证。由此看来,不难了解,柴胡证的活动面是如何的大,要是离开“证”的概念去对待他,显然都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我们再看103条:“太阳病,经过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此条指出,不仅柴胡证的范围大,而且,时间也特别长。《伤寒论》病变阶段的持续,恐怕还没有像这样的例子。有趣的人都可以算一算,没有一月,起码也是二十多天,但柴胡证仍在。
据以上部分条文分析,可以初步说明柴胡证的一般情况,从而了解证的基本概念。此外,还可以附带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论中常见到:“此本柴胡证”、“此非柴胡汤证”、“柴胡证仍在”、“柴胡汤证罢”、“若柴胡证不罢者”等等。何以柴胡证如此之多呢?又这样的常见?时间那样地长?涉及面那样的广?并且还公然提出“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前面谈过,仲景敢于下这样的结论,决非信口开河,无中生有。是真正抓到了柴胡证的本质----量多常见,范围大,为时长,处于枢纽地位,可进可出,向内向外都有充分的活动余地。当然,常见的东西,一定常见,这倒不怪。所怪的是这些本质特点,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和疾病作斗争的有利条件,即有易于周旋的良好机会。所以,在一个全能的医生面前,不仅能善于识别柴胡证和治疗柴胡证;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要会创造柴胡证和治疗柴胡证;因病制宜地广开方便之路。关于谈证的问题,扯得太远了,清楚与否,暂且撇开,下面开始谈四诊。
巳如上述,“证”是病人身上客观存在的东西,每一个病人都必须有其相对应的“证”存在着。这个证在一定的条件下又能反映出疾病的本质。但是,它总不会自已跑到医生的脑子里来。必须运用四诊或其他的诊断方法。从病人身上,无数纷繁的病情中去通过细集,微的收加以概括和组合,使之条理化,单纯化,归纳成我们所需要的“证”,才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四诊的第一个是望诊:《内经》云:“望而知之,谓之神,”张仲景也一开口便慨然叹秦越人“望齐侯之色”。这些都是强调了望诊的重要性。也是因为它是最先开始和最简 便实用,最正确的诊断方法。它的原理是本:“有诸内必行诸外”。有的医生仅凭望诊即可找到证的大半部分来,甚至有者,可初步建立理法方药,即所谓“望诊而得知”者。所以,也有人说,在诊断上最有实际意义的,没有比望诊再简捷可靠的了。
其次是问诊:问诊是了解证的又一个重要方法。许多疾病的原因及其内在联系,是既摸不出,也看不到的,只有问。仲景在《伤寒论》的序文里言道:“省疾问病”,说明病就是要省要问。问诊是基于语言这一交际工具,在双方很自然的思想交换下进行。大有不同于死板的对话过程。如《内经》所说:“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就是把问诊概入了平常的生活习惯。所谓问所便,无非是要问出病人最要求解决的问题。一个修养好的医生,三言两语就能够触动病人的心弦,道出他的苦楚,这就是病人所便。问诊要客观细微,不能主观臆断。记得黑格尔说过这样的话:“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哲学史讲演稿)。”医生虽然面对的不是古人,但也可不要像这样:如“白虎先生”问出来的都是些热病;“火神菩萨”了解到的就尽是些寒证。临床多了,会形成一种偏向,主观意识往往占上风,不独问诊,恐怕四诊都有可能。但决不是必然的客观规律,是可以改变,更能够避免的,只要有心注意。
再其次是闻诊:闻诊在中医的临床应用,似乎人们不太重视它。认为它实际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如江笔花说:“盖闻诊一道不过审其音之高低,以定虚实;嗽之闷爽,以定升降,其他无可闻者。”其实这些 都是错觉。人的语言改变,声音的异常,常是反映出机体很多病态的情况。《素问·全神论》说:“弦绝者,其声嘶败,……病深者,其声哕,”即是如此。闻诊的根据,也是本着“有诸内,必行诸外”原理。闻诊在记录病情的时候,实际也起到不少帮助和配合作用。例如:谵语和郑声,实则谵语,虚则郑声,这是谁都知道其以虚实即可辨别,其实不尽然,这是指明显者而言。有一种在听觉上非常模糊,似是而非。对闻诊没有经验的人,根本无法判断。要是一错,岂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吗?闻诊当然不只用耳,同时也用鼻嗅,这已不用说了,反正医生不是塞住鼻子看病的。载北山在《广温热论》上,对温病的辨识,还把辨病气列为第一项,并言:“非鼻观精者,不能辨之”。可见闻诊还是有用,应当掌握。
四诊的最后一个是切诊:切诊虽列为最后,但是,是中医非常讲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试观,有许多老中医的看病时间,都用在凝神贯气的切诊上面。某些传说,如:“悬丝吊脉”更把切诊神妙化了。经验多的临床医生,光凭切脉也有辨证处方的能力。实际上,也是这样,切脉所知道的东西,真是不少。《素问·脉要精微》说:“知内者,按而纪之。”意思是说:切脉一项,是集中了解病人的内部问题。人体内部的东西很多,除了目所能见的,皮毛以内,肌肉,腠理,筋骨,五脏,六腑,气血运行等都是。所以,脉须分三部九候,阴阳左右,脏腑排列以及表里浮沉等,就是用以候不同地方的情况。如《素问·三部九候》说:“人有三部,部有三候。”同时,人是活的,病更是要变的,见之于脉就有浮、沉、迟、数、弦、紧、滑、涩等诸脉的异常情况,还有人不是孤立的,他与外界环境必须统 一,随四时变化而变化,有小的变化,也有大的变化。小者如昼夜朝夕,情绪思维;大者如春夏秋冬,风雨寒暑。故脉也如此应之,而有平旦、日晡,四时诸脉。如《脉要精微》论:“持脉有道,春日浮,如鱼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又云:“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不可以为工也。”
总之,四诊的运用,是属于广泛地汇集病人资料,提供辨证之用,没有这一步工作或者这一步工作做得不好,我们就无证可辨,或者辨证不确,从而也就无法建立理法方药,病也就不能看下去。这步工作的重要性,好比进行生产建设一样,必须先准备好充足的生产用品和建筑材料,后面才能开工上马进行生产建设。四诊就像这样起到了准备资料,提供辨证的作用。当然,资料还只是一些素材,还要进行加工分析、综合使之成为“证”,才能提供辨证之用,这个上面已经谈过了。
三、牢固掌握八纲及其他辩证方法,把四诊所总结的全部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找到疾病的本质是完成理法方药的事实依据。
紧跟着四诊所要做的事就是“辨证”,把大批由四诊所汇集的病情资料加以条分理析的归类明确,最后确定理法方药,这就是所谓的辨证论治过程。辨证的方法很多,大一点说,凡是已经成立的中医学上的基本理论部分,如阴阳、五脏、脏腑、经络、营卫气血、三焦等都可以用来进行辨证。既能单独运用,也可以同时采取。不过,实际需要的还是“看菜吃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按具体病证选用一种的居多。比如,《伤寒论》是以六经辨证为主,杂病类则以五行及脏腑经络为主;温病则是以营卫、气血、三焦为主。而八纲辨证则又是属于一种综合性的,用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因此,向来以八纲辨证的方法算是最普遍和最适用的。八纲的内容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从临床上无数纷纭的病情概括出来的八类证群。其中阴阳又为八纲之总纲,运用起来更为广泛。故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表里寒热虚实皆可被其概括,如表证、实证、热证、就可归纳为阳证。里证、虚证、寒证就可归纳为阴证。余可类推。
先言虚实:八纲中除了阴阳外,虚实也是很重要的。治病时不辨虚实简直是无从下手。什么是虚实,《素问·通评虚实论》有一总括性的概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这两句话,常被称为“治病之大纲”。虚实的概念在这里是指的机体抗病力量的消长而言。故尽人皆说:“邪气无所谓虚”,当然也表明正气亦实。关于“邪气盛则实”,盛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实又如何的表现呢?那就是以病情作标准,正是机体抗病力量之强,才显得邪气之旺盛。用白虎汤、承气汤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既然能用上白虎承气汤之类,何虚之有。在正气实之下,处方用药都是一味的驱邪,没有扶正必要。汗吐下之 法,一般就用于这种场合,即邪气虽盛,而正气也没有衰减的情况。“精气夺则虚”,这句话好理解,当机体抗病力量走下坡路,以至无法支持的时候,就是虚,此时立法不仅要扶正驱邪,甚至还须采用大剂温补以拨乱反正,回阳救逆,驱邪则是以后的事了。有人说:“实是邪气有余,虚是正气不足,”也是这样的道理,只是说法不同罢了。邪气既无所谓虚,故只要正气能够和有余的邪气抗衡;或者处于平衡的对立状态下,就是实。当正气不足而衰退下来;或处于崩溃危急的时候,当然是虚了。关于虚实的实际运用,在某些情况下,概念是不一样的。如,《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里的虚和前面所指的虚就不相 同,那是基于病理学的观点,这里谈的病因学范畴。如果列入同一概念,这里就虚实皆不能成立。因为,未病之前是虚,既病之后当然更虚,尽是虚,一味的虚下去,也就没有虚了,因为虚实是对持的。没有虚就没有实,没有实当然没有虚了。《内经》又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本来大家都知道,邪气无所谓虚的,可是这里偏偏提出了“虚邪”二字,到底有没有虚邪?有,只要理解它是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同一概念,就必然有。虚邪贼风,就是指乘虚犯人的邪风,故与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相对应。又“邪风之至急如风雨”的邪风,正是虚邪贼风的简称,概皆列入病因学的概念。
表里:表里一般指病情的显现部位。也有人提出包括病势的轻重在内。在表者病轻,在里者病重,这样谈本来是可以,不过会造成一些辨证时的混淆,因为,表病不一定就是轻病,也有重病在内。而里病也并非专指重病,也有轻病。同时,表里的相对性很大,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东西本无定论,何况表里当转换的时候,而轻重就不一定也跟随不变。例如,表病转里,有时就不是由轻到重。《伤寒论》有一条:“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按部位是由表及里,但按病情则是由重转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所以,还是分别对待的好。还有,单纯的表证,多半由外解,这是常法,而表里证同时存在时,就须得斟酌情况,有所抉择了。《伤寒论》就有表里同病,急先救里的变法。再说:表病是病情集中表现在外表,里病是病情集中显示在体内,究竟什么地方才算表,什么地方才算里,看起来是很难划出严格的分界线。但是,当我们用作辨证的时候,从症状的显露上,有些时候就表里清楚而界限分明。所以就此问题有人提出来说:孤立的八纲辨证,不能具体的解决问题,必须同时结合症状才能切合实际。例如,《伤寒论》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难,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此条表里症就是界线分明的,手足冷以上为表证,心下满以下为里证,谁都认得出来。但是,如果撇开症状,单独告诉,此有表复有里,就谁也无法推导出确切的症状来,更不能说处方用药了,本条后面接着说:“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下面再说:“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这两段话,皆撇开“表”字而谈“外”字,究竟表与外有没有区别,这是常常使人模糊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言“外”才是强调部位,言“表” 只是归纳证状(就此处看)。因为,表证一定在外,这是无疑的。但把外证当作表证,就未免不够准确了。表证与外证才是有程度不同、轻重之分。比如说,外证里既可用桂枝汤,也可用柴胡汤(146条的柴胡桂枝汤证,就是这个例子,那里也言外而不言表)。但在单纯表证时,而桂枝汤当然可用,但如果用小柴胡汤就不恰当了。我们是谈的辨证,辨证当然要求愈准确愈好。
寒热:寒热是代表病性的。病情的性质属寒还是属热,常常是左右理法、变更方药的关键所在。有人将它同体温的变化结合起来,这样,在观察上是带来一些方便,但也有因此而拙笨的。因为,寒热从性质的理解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寒就是寒,热就是热;寒的时候,体温一定会下降,热的时候体温一定会上升;相反过来,温度升高就是热,温度下降必定为寒。其实这只能对付自然界的一般物理现象,在病人身上就大有不同了。不仅寒热可以错杂交混各不干犯,而且可以互相依赖,长期共存。厥阴病和湿温病就是这种典型的情 况。还有,寒热不光是错杂共存,而且真假不一。“阳盛则热,阴盛则寒”显然指的单纯的寒热,而“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 ”,虽也指单纯寒热,但就有本质上的差异和真假的区别了。关于真假寒热,不仅辩别上存在许多困难,就是在治疗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下面有两个简略的病案可以帮助我们认别寒热,尤其是真假。
1、喻嘉言治一人:“伤寒六七日,身热目赤索水至前不能饮。异常火燥,门牖洞启,身卧地上,展转不安,更欲入井。”以上情况不加辨证,多少人会认成大热之证,如要考体温,恐怕也只有高,不会低。但是,我们看下面怎样的治法:“以大剂人参、姜、附、甘草
煎汤冷服,服后寒战戛齿有声,阳虚之状始著,以重棉和头覆之,更与一剂,汗出热退而安。”
2、徐灵胎医案:“ 洞庭卜夫人,患寒疾,有名医进以参附,日以为常。十年以来,服附子数十斤,而寒愈剧。初冬即四面围火,绵衣几重,寒栗如故。余日:‘此邪并于内,逼阴于外’,《内经》云:‘热深厥亦深’, 又云:‘热极生寒,故其热使达于外’。用芦根数两,煎清凉疏散之药饮之,三剂而去火,十剂而减衣。”
此外,谈一谈:一个医生由接触病人开始,到他完成理法方药,中间一段工作过程,说起来很长,做起来也艰巨。但是,在一个具有丰富的临床医生面前,简直是极其寻常的事情。要处理一患者,根本用不了多少时间,而且准确恰当,可以说多快好省。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熟能生巧是一个条件。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个临床体系,这个临床体系是什么?大概也不外乎把辨证施治法则,以及四诊八纲整个内容来一个有机联系,加以系统化了的缘故。所谓系统化,举这样一例子,大概可以明白:,在检阅部队的时候,士兵中,有掉了一个扣子的,他都能看出来。而在他未来之前的某些,虽然也曾作过预 检工作。可是就不可能发现。这是什么道理?很显然,这是他有一套系统的检阅方式。所以,一个医生在面对当前的病人时,应该怎样进行诊断,治疗;如何运用辨证施治,必须有一定的系统性。,学到能发现一个扣子的本领去检查病人,发现更多的问题,掌握更全面的资料。资料是不嫌多的,越多越好。但要避免抓住芝麻,丢掉西瓜。
四、理法方药的形成及其实践意义
我们已经明确了,无论哪一个病,或哪一个证,它的正确的理法方药的成立。必须奠基于对证的真实判断上。反过来也只有理法方药的直接形成和准确无误,才可能实际的完完全全的处理好一个病或一个证。
关于理:理是什么呢?就是以一系列的客观事实,以现存的病情资料作根据,来证明 疾病的性质,从而医生据此作出对病证的判断。医生的判断是病情资料和医生观点的统一表现 。因为,有了病情资料,然后才有理论根据;有了医生观点,然后才可能得出结论。论据是用来说明观点的,而观点又必须资料作证明,这就是完成“理”的过程。比如,在某个病人身上,所求得的病情资料中有:舌质红绛、神昏谵语、脉数烦燥几项主要病情资料。这是病人身上的东西,是理论和事实根据。有了论据,医生就可以判断。按照温病学,以营卫气血的辨证方法,这个判断就应该是“邪入营分”。判断是医生下的,当然就表明了医生的观点。下面该 采用什么法则,医生就据这个判断去决定。
关于法:法就是“法则”,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是解决矛盾的实际体现。正如上面所 下的判断“邪入营分”。营是什么?已经知道。邪入了营分,这是矛盾的焦点,因为营是不容邪入内的。但邪又偏偏入了,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把邪从营分清除掉。那么它体现的法则,很自然是“清营解毒”。因为只有清营解毒才能合乎这种要求,不清营解毒当然不行,客观现实需要这样做。致于法,为了应付极其纷繁的客观要求,当然不是简单几项所能胜任的。因此,在中医学上,法的体现形式也是非常繁多。别的不说了,其中主要的一种,如“正反”或“逆从”,是比较突出的一种。不过仅管形式多样,万变不离其宗。本质要求只有一个——具体的解决矛盾。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按所对应证的现象不同应用不同而已。孙思邈说过:“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就是从本质和现象来观察它所发生的差异,有此差异的时候,法则应该采取不同的来对付。在正反法则上的最基本的应用,就是对付这种本质与现象不符合而出现差异的情况。如治热以寒,治寒以热,这是正治。何为正治?药与病相反也。药与病相反,是反映本质和现象的一致性。寒病现寒象,热病现热象,就是一致。又治热用热,治寒用寒,是谓反治。何谓反治?药与病相同也。药与病相同,反映本质和现象的不一致。像“甘温除大热”的病状就不一致,其内虚而外反热,当然不一致。何以知其不一致,因为这个大热,不是真正的大热。真正的大热,应该用“苦寒”,那会用“甘温”。关于正反法则的运用有这样一条简单规律:大概的病,在初期轻浅者,常是本质与现象相一致的时候居多。此时也多半进行逆治法(正治)。如麻、桂、青龙、白虎、承气汤类的病证,属于三阳范围者,都是以热治寒,以寒治热。病到了未期,或者经过多种错治,造成病情复杂深重时就常会出现假象,本质和现象不一致。此时多半就采用从治法(反治)。如四逆、通脉、白通、麻黄升麻诸汤以及所谓“引火归原”、温补之剂等。属于三阴虚损病类者,就是以热对热的方法。《内经》谓“甚者从之,微者逆之”,大概就是指的此类情况。
前已述及,理法方药是一个整体,跟随着 理法的建立,方药也要相应地产生,有理就该有法,有法必然有方,有方肯定会有药。这一连串的经过,好像流水似的不受阻碍,一直流下去。可是,“看着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尽管理法已经成立,要把方药准确而完美地接上去,还必须付出许多的辛勤劳动。理法方药既然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那么,疗效就全凭这点生气,像血液循环一样,贯穿在它的全体。无论那一环节发生故障,毫无疑问,都将影响整个疗效,这个问题应当怎样去了解?我们不妨多加留心一下,去思考那些所谓通不过疗效关或者存在有问题的每个方和药,就不难看出这样的一些情况,如脱离辨证的、割裂理法的、断方取药的、模棱两可的 、五味具全的还有就是像“开药铺”的、“亮家当”和用大方打大围剿的等等。谁也不敢全信,药味既非常之多,又样样都很精当。现时提倡医、药结合,更不应该这样。我们说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做文章是如此,开方子恐怕也要这样,该用则用,不该用最好从简。所谓“要言不繁”,“要方不杂”,经方不是很好的例子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情况,虽然不甚关立法处方的事。但也有违背理法方药的趋势。故也值得谈一谈。一种是所谓“一方多剂”,动辄一个处方,一次就给病人开上七剂、八剂,乃至二、三十剂,连续服下去,一成就不变,一去不再来。这看起好像很关心患者。
其实,那里是真正在治病,全是一种丧失责任感的表现。同时,三岁孩子都知道,药是不好吃的,“良药苦口利于病”本来就有点勉强的了,再来一个既非良药,仍然苦口,又不利于病,岂不明明叫人受活罪,“大吃其苦”吗?因为,除了极少数的病例外,大多数的病服药后,不是好了,也得变了。另一种是所谓“服养生药者”,认补药为良方,良方当然是补药。还说什么:“常人之情,皆贵补而恶攻”,这种情况和上一种差不多,完全是迎合病人,医生没有一点权利了。因此,我们为了保证理法方药的纯洁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就必须坚持辨证论治下的处方和用药,要先辨证,然后论治,不仅证要辨,连治也要辨,必要时还要一个一个的方辨,或一味一味的药辨。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辨证和割裂理法方药的现象。把每一方每一药都提到高度的准确程度。
有人认为,理法方药很抽象,不好具体贯彻。抽象是说它完全是一些概括性的空洞结果。目标在哪里,应在哪一个人身上还得去找,但其实只要找准了,就非常具体。具体是指它完全按照摆在医生面前的那个病人身上的实际需要制定下来的理和法,选出来的方和药。不偏不倚正应在他的身上。要是认为不是这样,可以试想:一个医生尽管他塞满肚子的方和药,在没有理法的指导下,方和药能使得出来吗?许多人反对“隔山开药(不见病人的处方)”就是这个道理。再说,一个多年开中药房的老先生,他所配的方和药也是多得惊人的。但是就是没有人去专门找他看病。同样一个全付武装的士兵,要是迷失了方向,分不清敌我,不知为谁而战,打起仗来,又当如何?所以,方药必须服从理法范围的支配,更应该符合辨证的要求,才真正的发挥应有的作用。所谓 “遣方用药”也必须接受辩证的遣;服从理法的用。“对症下药”也只有真正的对好症,方才允许下药。不仅如此,就是在某些理法方药都成立的情况下,只是在剂型有所改变,还是不够妥当。《伤寒论》105条:“伤寒十三日,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不利者,大便当鞭,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本条前面言汤下之,后面以丸下之,仅一字之差,汤丸之别,竟遭全盘否定“非其治也”。由此可见,保持理法方药的健全性,是多么重要的事。关于方:方是把多种药物照按一定的组合原则,而构成的一种形式。这个组合原则,就是“君臣佐使”。如《内经至真要大论》言:“主药之谓君,佐君之谓臣,佐臣之谓使。”君药必须是方中之主导药,起主宰作用。如麻黄汤里的麻黄,桂枝汤里的桂枝。臣药与佐药都是相辅协调的药物,是用来解决兼证或调和各药之间的矛盾。一个方的组成,不管其君臣佐使如何变更法,如君一臣二,臣三佐五,臣五佐九等,都是基于他们之间的彼此关联性而利用其群力的发挥的一种作用表现。这种相互关系表现在质的变化,如诸种建中汤的应用,量的变化,如承气与厚朴三物汤的情况,型的变化,如汤与丸散的改变,以及煎服法和先后次序等。所谓“方成无药”大概就是通过这些变化后,把单个药物改头换面,集中到另一条道路上去了。临证时,除了在随机应变的特殊情况下,必须自已组方更药外,“方”一般说来,都不是临时拼凑的。大多数的医者,都习惯于胸有成竹地选用适合的成方,或者略加增减。因为,在几千年的中医发展史上,古人已给我们创立了无数的良方妙剂可应无穷之变。但这里也得知道,关于选用成方这一点,决不能与朱丹溪所批判的:“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异,幸其偶然中,难矣。”混而为一。丹溪所谓的是他所说:“据证验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的不经辨证,脱离医者的教条和经验主义者,当然与此有本质的区别。明乎此后,中医为甚一贯既允许所谓“医不执方合宜而用”、或“师其法而不混其方”的“治病悉合乎机理”之灵活做法;又要强调按照 常规选用成方的“论方不流于偏僻”的诫律遵守,当然不是也从来不作那些无谓的拘泥和绝对的崇古。相反,这种做法还内容丰富,花样奇多。只要没有违背中医遣方用药的特色—君臣佐使和复方的综合原则。这些做法是完全可以,而且是必要的。但也该避免像张元素那样:“古方新病,不相宜也”的完全否定性的武断。如果离开了方药的组合原则,标新立异,单纯去刁选药味的美妙,就成为“有药无方,华而不实”了。在这里张仲景先生又永远为我们的典范。他不仅是创造辨证施治,联合理法方药的鼻祖,而且也是方随证变,药随方施,百般灵活不守死法的标准人物。大论中有一条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就是这种手法的突出表现。有人死咬住桂枝汤方不放,而否认那有枝汤方去桂枝君药的道理。其实一经化裁加减,它那里还在桂枝汤方的那个圈子里呢?所以,我们无论在执行一个完全的成方也好,或是组合某些复合的方剂也好。一定要有的放矢,量体裁衣,既不能犯教条,顺手拈来,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也不要过于冒进,大刀阔斧,盲目的剪裁。一定要既胆大而又心细地对症下药深思远虑,一切为患者出发。我曾看到一些老中医,在他的处方上印着“剑胆琴心”四个字,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图。
为了能够有效地克服上述倾向,稳步地进行在正确的理法方药道路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帮助方法可以试行。就是从方剂到药,由药到方,仿照大脑皮层的机能一样,建立一个分析与综合的过程。这其实也是常听人说:把理法方药熔在一炉的办法。这个方法怎么做法,下面分析一个方药,或者可以达到启发。就以六味地黄汤来说吧,这个方是一个公认的滋阴妙剂,是由金匮肾气丸脱胎出来。自钱仲阳以后,历代的加减化裁更是盛极医界。但是,它的妙处妙在什么地方?虽然见仁见智各有千秋,但基本方向不会太远。本方的主药为地黄和山茱萸两味,是用以解决阴虚液亏的主要矛盾。其余药物都是围绕这两味主药而各尽其能。我们知道,阴虚常伴有血热现象,所谓“阴虚生内热”是也。牡丹皮佐地黄、山茱萸能够凉血清热,泻阴虚之火。又知道,滋阴药每每碍于脾胃,影响消化,所谓“滋腻害胃”是也。山药是一味具有良好的健胃而不滋腻的药物。同时,也就可以克服碍胃这一缺点。最后,我们更了解,滋阴药的目的,是求得“增津壮水” 。但增津壮水,也该有他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是有害的。正如“发汗”不可如水流漓,“攻积”勿令至大泄下一样。但是,万一超过这个限度怎么办?此时,就有赖于茯苓、泽泻为它找寻一条巧妙的出路,防患于未然。同时,苓、泽还富有“推陈致新”和“求南风开北牖”之意。当然这种分析只能概括一般,细微之处及临证的差别是各有不同的。致于分析正确与否那更是次要的问题。目的在于运用 这种方法,不仅使我们较好地选方择药,而且借此可鉴别方剂的优劣;更重要的是锻炼我们掌握组合方剂之技巧,同时克服偏向,走向熔烩理法方药的地步。此外,还谈谈:上面说到的关于选方用药一事,虽然只提到对成方的选用。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的减弱每个医生自已创造新型方剂的作用。相反,这还是中医的优良传统和高贵的精神,应当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们说:用方并不是用钞票,自已不可以制造。钞票当然不可以自已造,自已造要犯法。不过也该明白,造方虽然不犯法,但粗制滥造,造错了,拿去医死人就得犯法。那么,是不是还是小心点,不造的好,永远享古人的福。又不是,因为那样,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方就会越来越感不够用,就会停滞不前。我们知道,《伤寒论》才一百一十三方,加上《金匮要略》和一些古老的一齐算,也不过两三百方。但是,现在有多少方了,恐怕谁也算不出来。这些方那里来的,还不是后人造出来的吗?当然,其中是有程度不同和好劣不等的。不过能够通行,用之有效大概都有是好的。像刘河间的“双解散”,吴又可的“达原饮”,喻嘉言的“清燥救肺汤”,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等举不胜举,不都是鼎鼎有名的好方吗?我们学院卓雨农老师的《妇科学》上,有不少自制方很解决问题,大家都喜欢用。所以,凡是一个合格的医生,都该有造方的能力,而且也必须有这样的能力。
关于药:谈到药,我们都会联想到,神农嗜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因为,只有经过嗜,才能知道药的味;也只有遇了毒,才能晓得它的性。中医的气味学说还不是嗜出来的吗?用气味学说来解释中药的药理作用,已经是几千年迄今为止的一贯主张了。这个观点,并构成了祖国医学上药物方面的一个重要理论组成部分。四气和五味的综合,更加概括了一切药物的性能作用。所谓:“气味之所在,即性用之所在”是也。如甘、苦、酸、辛、咸构成的五味,就表现了五种不同的药理作用。甘具有缓和与滋补的作用;苦具有泻下和燥湿的作;酸具有收敛和固湿的作用;辛具有行气和发散作用。寒、热、温、凉构成的四气,表现了药物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四种不同功能。如治热病的药物,具有寒凉性质;治寒病的药物具有温热的性质;寒与凉,温与热,又在于它们之间程度上的不同。如微寒则为凉;大温则变成热了。药物除了气味之说以外,还有所谓:升、降、浮、沉的说法。如李东垣云:“药有升降浮沉”。不过这也是把气味学说加以推衍发挥而已。如气薄者升,味厚者沉,气薄者浮、气厚者降,皆离不开气味二字。又升有升散之意,降有平逆之意,浮有上行之意,沉有下行之意。总之也不过在味气外又加入一个药物的趋势罢了。关于四气的性能,在方药本身是不能表现的,必须在和机体发生作用之下方能显示。如白虎汤与四逆汤两方的寒与热不是温度计可以量出来的。就是五味也那能离开人们的感官呢。由此可见,一切方药的功能作用,都是属于气与味的综合,同时通过药与人的关系而体现出来。如辛与温相结合成了辛温,用之于人可显示发汗解表的功用,银翘散、桑菊饮是也。辛与热相结合成了辛热,用之于人有温中回阳作用,四逆汤、白通汤是也。苦与寒相结合成了苦寒,用之于人有清热解毒作用,黄连解毒汤是也。寒与咸相结合成了咸寒,用之于人有泻热解毒功用,大小承气汤是也。甘与寒相结合成了甘寒,用之于人有解热除烦作用,人参白虎汤是也。苦与辛相合成了苦辛,用之于人有杀虫止痢作用,乌梅丸是也。余皆以此类推演变无穷。
药物除了分属于四气五味之外还不能不谈,尚有一类味淡、性平和者。因为不便归于以上范围,故常将其另立一类。不过也有将其并入五味而为六味五气者 。这一类药物,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多数医家颇感兴趣的一种,常常被作为盲目选用的对象。其理由是因为毒性 低很平正王道,能迎合“清心寡过”意愿,即或用错了,也不会发生好大的问题。但是也不能不知道,这类药物从表面看来是气平而味淡,有时确也可以稍微放松考虑。然而要想真正得到如许愿望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中药治病,除了真正的单方之外,按它的特点,都半要经多味组合的。既经组合,再经内服而与机体发生作用,就无论如何也不会绝对风平浪静安如泰山。朱丹溪说过“清香美味,诚足可口,揆之气化,恐未必然”。喻嘉言也说:“凡药皆能伤人”。所以,那些迷信平淡方和陈修园所说爱用果子药者,有时就是不平淡,更不会象果子。仅仅是相对之下,有所缓和而已。要是闭上眼睛,张冠李戴,随时都 可以闯下奇灾大祸。王叔和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此话是何等的警世。所以曾吓得有些医家对桂枝终身不敢问津。可是这里,我们能单纯的怪桂枝的不平淡吗?诚然不容忽视,桂枝性属辛温,阳证禁用。然而据《神农本草经》的记载情况又不仅如此,桂枝尚能补中益气,久服通神,轻身不老。即是说还能有延年益寿,是养生上品。但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杀人之物?很显然,这就是药不对症。药不对症是医家之大忌,任何清淡药都不可能逃此公例。前已道及,一切方药归根到底都是辨证论治之下的产物,当它一旦按照理法的差遣,就能斩关夺将去完成它的任务。要治病就不能不备治病之力。力虽有大小,但总归有力。这个力,有病则病受,无病呢?《内经》不是说过吗?“有故无殒”。无故呢?他没有说。不过,不说也是知道的。当然,这里的故,是指对症的故,不对症的故再多也等于无。由此看来,真正的清淡方“果子药”是不可能存在的。即或有也不该归在医学范畴,而是属于饮食行业的事了。朱丹溪还有一段话(载在《局方发挥》里)颇有意思。那些爱以清淡为常,喜欢用果子药者,不妨看一看。他说:“谓之余利别者,皆取时果之液,煎熬如饧而饮之。稠之甚者,调以沸汤。南人名之曰煎,味虽甘美。性非中和。且如金樱煎之缩小便,杏煎 、杨梅煎、蒲桃煎之发冒火积。其余味之美者,并是嬉笑作恶,然乎、否乎。”这段话的意思,已不言而喻,充分道出了果子药之时弊。
我们说,每个病证都该有自己最适宜的方药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方药,医生就得创造这样的方药,责无傍贷,决不能敷衍塞责,贫图便利,清淡过关。《内经》上说的:“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 的对药病关系的一般规则,我们未尚不可这样理解:这不是在几千年前就给我们明确提出了医者的功故问题吗?也就是说方药越准确无误,则毒性会越来越小(不能理解为越无毒才越好),毒性越小,则效果越可以提高而形成正比关系。反之,效果越降低,则毒性相应就越增大,毒性增大了,其方药就越应当注意不可轻易妄用。所以如果单纯认为方药越平淡无毒,则越可放手施用,越放手施用,则疗效就越能不断提高,那就糟了,恐怕何不去“喝西北风”岂不更好,还要谈什么遗方用药?因此,一个临床医生,在建立理法方药的同时所想到的:除了必须紧紧依靠辨证论治之外,更应该深深考虑到方药的功与故问题(疗效及其毒性或副作用)。不要认为有了理法方药之后,就万事大吉,再不顾问其后果了。谁都知道,“用药如用兵”,方药好比一种兵器,用其杀人还是救人,就看掌握在庸医还是良医手里。只有用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郑重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救死扶伤意识,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变于无穷。《内经》以阴阳定“生杀之本始”,医生虽然不是纯阴阳家,但的确在一定情况下能够操纵着病人生死大权,左右阴阳之道。“人命关天”自古尤然,只有在树立“一切从人民健康出发,,才不失为真正的人民健康捍卫者。
未了,谈谈理法方药的实际意义。已如上述,理法方药是直接形成于“论治”的过程,而论治过程也正是治疗工作落实的过程。但是简单言“论治”二字,仅是一个空洞的筐子。必须还要装进理法方药的具体内容,才能切合实际,付诸实践。然而理法方药也不是无本之,无源之水,必须有它一定的建立过程,这在前面已谈得够多了。不过为了进一步了解理法方药的实践意义,还得略为回顾一下某些辨证方法的内容。众所周知,无论以八纲辨证也 好,脏腑经络辨证也好,或营卫气血、三焦辨证也好,等等。它所能回答的问题,再多也不过言道:表里阴阳卫气营血脏腑经络一些极为笼统的概念。医生要是企图就以这些单一的概念用于临床上,就能够准确无误地指导理法方药的完成,那是有困难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比如说,光是告诉一位医生辨证的结果是“表寒证”,试问这位医生能恰如其分的就此“表寒证”三字而开出一个很好的方药来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所得到的只是一个笼统的表寒概念,而治表寒的方又是那样之多,究竟叫他选用哪一个好呢?当然不能也不可能会一概的用上麻黄汤或九味羌活汤之类,也不可能光靠麻黄汤,九味羌活汤就能概治一切表寒证。这中间要有一个重要的思考过程,也就是有所抉择。但是抉择要有根据的抉择,根据在什地方?前面说过靠寒热几个字是办不到的。那就是仍然要回转去必须结合那些所谓的单个的症状和体征。例如要选用麻黄汤,就该想到病人是不是有脉浮、发热恶寒、腰痛、骨节疼痛、无汗或喘等。这些症状也只有在已经出现了才可能去选用麻黄汤。要是这中间有不符合之处,那怕只有一点不对头,如无汗变成有汗,脉浮变成脉沉。那么麻黄汤肯定不适用了(甚至所当禁),必须另行更方或者换药。由此看来,单独的症状有时对于建立理法方药还起到决定性作用,不是光靠几个含糊笼统的辨证概念所能完成得了的事情。当然辨证的过程也是对于单独症状的分析、归纳,而“证”的概念也正是这个分析归纳的结果。但不管怎样它不会永远脱离理法方药,就能具体指导临床实践。只有准确的建成了理法方药这一完整的治疗体系以后,才能实际的体现“辨证论治”的精神使之成为现实意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