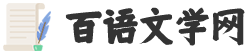采写 / Moking
这是HumanStory第13篇文章
他说 :“在我的作品里面会有很多女性角色,特别是对女性身体过度直观的描绘,而且通常视觉上呈现出来的都很“恶心”,比如内脏器官、残肢、淌着泪的笑颜、空洞的眼睛、兴奋得抽搐的肉体等。我想我画出来的这些女性身体应该不是为了愉悦自我或者他人,而是想尝试跳出自己的男性视角,做到“去欲望化”的呈现。”
▽ 把烂到骨子里的东西赤裸裸掰开来看
我今年30岁,是个自由职业者,插画师。从进入美术特长班算起,我画画至今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
我的作品没有一个核心表达的主题,只能说是自己所有感兴趣和思考内容的合集——通过对暴力、欲望、两性关系的描绘,来展现中国语境下集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不确定我想表达的跟我实际呈现出来,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在我的作品里面会有很多女性角色,特别是对女性身体过度直观的描绘,而且通常视觉上呈现出来的都很“恶心”,比如内脏器官、残肢、淌着泪的笑颜、空洞的眼睛、兴奋得抽搐的肉体等。我想我画出来的这些女性身体应该不是为了愉悦自我或者他人,而是想尝试跳出自己的男性视角,做到“去欲望化”的呈现。当然,这种“去欲望化”的视角可能不纯粹,毕竟自己本身的性别身份无法抹除,所以会不经意间把理想女性的想象投射到作品中——这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距。但是不管怎样,至少在绘画上,我是有这样的意图的。
你说看了我的作品,发现在15年之后,内容和风格上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嗯,其实我作品的变化从来没中断过。
我刚进入广州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在绘画上是比较注重写实的,就是想着怎么画得更逼真,很在乎作品或者描绘对象在写实层面的趋近。因为中国近代的美术教育传承了苏联那一套的理念,在集体主义的大框架下,文艺作品的目的就是实现对人民的教化及动员作用。所以这种美术教育理念培养出来的艺术表达,在结果上往往是最大程度地遮蔽甚至抹杀个体的权利和欲望。刚刚进入到美院创作体系的学生很容易被这套理念带着走,从而坠入到现实主义单一美学的牢笼,在大一、大二那段时间我自己也不能避免。
但是在我大二下半年的时候,大概是08年吧,我的作品才开始跳出原来的这种视觉表达,在绘画上逐渐探索出自己的风格。这种变化当然是有原因的。
当时我开始尝试通过互联网去接触一些外界的资讯,从那个时候自己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美学思维和视野被空前拓宽。包括在微博上,你会看到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扮演着文化掮客的角色,不断地从外界翻译一些资讯过来,为我们提供看待世界的另一个视角。通过这个过程,我了解到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另一面。
同时我也通过阅读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思维。因为中学教材对人的思维桎梏太深了,如果不看课外书,你的视野无法触及到主流叙事外的其它角落。那么课本或者主流信息渠道提供的那套权威话语和逻辑就会占据你的认知,那套陈词滥调的世界观就会成为你认知世界的唯一切口。当然,现在看来,那时候汲取的知识和资讯也存在偏颇,但它起码帮助我建立一套更科学有效的思考方法。
正是基于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思考,我的作品才开始尝试用戏谑或者反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或许狭隘但旺盛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切入点就是对集体主义的怀疑及反思,把集体主义狂热下那种压抑和绝望的氛围呈现出来。如果你看了我那个时期的作品,就会发现我在里面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符号”,然后通过腾挪、并置的方式,把一些让人不怎么愉悦和舒服的东西赤裸裸地掰开给大家看。
打个不确切的比方,那个时候我的作品有点像韩寒早期的杂文,他的文章无疑就是在那里玩反讽的游戏,当然,这种过剩的讥讽和过于符号化的堆砌很容易让批判本身失去力量,徒剩游戏的快感。我早期的作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为反讽而反讽,直白而空洞。
后来15年的时候,因为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创作上过于直白的社会表达行不通了,所以我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上又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身体快感和暴力的描绘上做得更极致,类似B级里那种恶趣味的东西变成我新的关注点。不过在这种恶趣味的表皮底下,我会夹带私货,放进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以此来找到平衡点。
最近我开始关注性别的议题,也看了很多相关的内容。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好莱坞电影圈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先是有好莱坞女星及女权主义者举行“反性骚扰”活动,然后最早掀起性解放运动的法国女权主义者开始反对“反性骚扰”这场活动的过渡演绎。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有一批人跟着去反对“反性骚扰”的活动,我就觉得特别好玩。我在想:在这个现阶段还存在严重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教育落后的环境中,去反对“反性骚扰”是否真的合适?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接下来性别议题也将会是我作品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想呈现两性之间的差异和张力,以及这种张力与社会其他议题的互动。
▽ 校园暴力让我用边缘人方式思考问题
关于我的作品为什么会聚焦在暴力、欲望和两性上,这个问题是我创作上很少直面的,这也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我的求学生涯中,校园暴力和教育制度的不公现象一直以各种方式轮番上演。如果你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的东西,我想应该是在亲眼目睹女同学被欺凌开始的吧。那个时候校园里最常发生的事情——“不漂亮”的女生被嘲笑,“漂亮”的女生被猥亵。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读五、六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女生身体发育比较快,结果因为这种过于明显的性征,让她成为班上群嘲的对象,班上那些“坏男生”对她的欺凌和羞辱更是家常便饭,比如把她的书包扔到地上踩,踹翻她的课桌,甚至是不怀好意的身体推搡,而这个女孩的反应只有神经质的冷笑和啜泣。到了初中,我就经常看到班上一帮“烂仔”对坐在课室最后一排的一位肥胖女生进行嘲笑和捉弄。这种事情持续了三年,他们毫不厌倦。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思想也变得比较极端,对人性恶的想法占据我的大脑。我发现,读书好的学生因为忙于学习是不会有空去欺凌弱者的;而那些读书不好的学生,而且通常是学习成绩靠后的男生,在班上则往往扮演凌霸者的角色。当时的我会在学校布置的周记作业里写一些很偏激的文章,比如说学习成绩的优劣是人优秀与否的标准,女性也应该欺凌男性中的弱者,道德极度低下的人应该被铲除等。
这种想法一度引起了老师的担心,但是当时真的太恼火了。现在想想,大概是自己无处排解的道德焦虑和不健全的世界观在作怪吧。不过如果用我的那套道德标准去衡量,自以为更有良知的人应该去帮助这些被欺负的女生才对,但是我没有,我也担心自己和她们靠得太近会遭受同样的羞辱和欺凌。事实上,读初中的时候我因为身体瘦弱,行为举止不够男性化也被嘲笑过。所有的这些经历,都让我开始会用边缘人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我记得高中报了美术特长班之后,我开始观看大量的电影,尤其是电影世界中形形色色的边缘人生活。也是在这个时候,女性主义这方面的认知被不断地强化,自己也开始从电影和动画上去分析——女性图像在被观看过程中——产生的道德问题。包括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女性图像在动漫作品中的被物化》也跟这个有关,我发现女性在现代消费社会的图像生产中,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被动的、去自我意识的角色存在。
巧合的是,我现在也成为一个女性图像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而且把这一层的思考和想法置入作品当中也变成我创作的一种趣味。不过现在我面临新的问题——我的作品是否也存在着对女性的异化?因为这种异化是不自知的,你下载或者翻阅时尚杂志,甚至看户外广告牌,这些消费女性图像的过程中,你其实都参与进了对这一性别的物化和剥削,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区别只在于这种参与的剥削性有多大。所以目前我对这个问题是自知而警惕的,但不妨碍我在创作过程中的对象选择。
你问我会不会担心读者对我作品的喜好只是出于一种猎奇心理,这个我不担心。说实话,其实我对自己作品的感受也可能含有很大的猎奇成分。比如我刚才提到我的作品会尝试做到“反愉悦”和“去快感”,但是这种东西本身也在制造猎奇,也不可避免地会激发另一种层面的快感和愉悦。我把恶心的东西表达出来,但是这种恶心的东西也让人爽啊,所以说人的欲望是复杂的。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为什么像《战狼2》这种充满血浆和杀戮的电影也可以卖几十亿,说明人内心对暴力是有憧憬的,或者说对让自己不适的东西是有追求的。回到我的作品来,它本身也有我对欲望的宣泄,只是里面可能隔了一层反思的东西而已。
至于你说我的作品能不能和受众读者产生共鸣,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以现在我无人问津的名气,我想关注我作品的人大概都是对我作品感兴趣,主动想跟这些作品建立认知链接的人吧。如果有一天我的作品变成收藏家等待升值的投资,你说的这个问题才会成立——你会担心买你的画的人不懂你。但是现在关注我作品的人,基本是了解和感兴趣的。哪怕那些声称看得不太懂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看懂看不懂,我想他们也都会有进一步了解的冲动。
有时候想想,对我作品的解读,也有可能是你在尝试自我阐释的过程中附加上去的。坦白说,我在作品成型前并没有那么清晰的思考和理念,创作的过程总是被感性的美学冲动和情绪占据着。想得更多的反而是上面需要放什么、怎么构图、然后如何对接一些我的趣味和情绪,很少说事先就定好一个明确的主题。
当然,除了这种绝对自由和个人化的创作以外,我也很享受跟其他创作者跨界合作,或者是有一定自由度的商业创作。比如我在跟一些乐队或者唱片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就会被事先告知一个明确的主题或者要求——我需要一个女人被一堆男人膜拜,你给我画。那我就会在这个基础概念上进行拓展和填充,整个创作过程也需要不断跟甲方磨合。
谈到生计的问题,收入当然也是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经常面对的困扰。目前我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个叫“奇点画廊”的艺术空间和一个“起点艺术节”的品牌,我们会把一些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在这个空间进行展示、推广和售卖,这个艺术空间囊括了画廊、创作作坊和工作室等功能。这些作品从绘画、独立漫画、zine到摄影和影像,不一而足。国内外都有很多以独立状态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他们需要有更专业的平台来展示和推广他们的作品,而且市场对于这种偏地下状态的艺术也是有一定需求的,所以我们打算搭建一个跨国际的平台,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期望“奇点”在填补这块地下艺术的空白的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自由创作人的生存困境。
▽ 我如何在中国式的父子关系下取舍
说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经常调侃说:“你的作品这么另类甚至‘病态’,是不是家人对偏激艺术的接受能力也异于常人?”其实刚好相反,我是生长在一个相当保守的传统中国式家庭。我父母对自己创作的态度是置之不理,任其发展。
所以在朋友圈分享画作的时候,我会刻意把一些觉得尺度比较大的作品,在父母面前进行选择性屏蔽,让他们只能看到我部分尺度比较小的作品。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我妈也会抱怨说:“你怎么老是画这些神神鬼鬼的公仔,让人很不舒服。”他们的观感就是——我的东西让人很不适。
反而是我女朋友她爸妈会表现出对我作品的兴趣,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吧。但是聊到我的作品,他们也会有“你的东西怎么那么灰暗”的疑问。他们这一辈的人对艺术的理解还是很主流的——认为艺术应该是让人愉悦的,抚平你的内心的东西。我对此尝试过进行解释,至于他们接受与否,其实并不重要。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审美偏好,它无关高下雅俗,有时候仅仅是趣味的差别而已。
你问我在绘画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家庭力量的阻碍。我记得我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爸还想让我回去当中学教师,因为我大学主修的是美术教育,还特意让我堂哥帮忙去找学校关系。但是大学时期我也算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想妥协。当时他的说法是:“等你结婚后,就知道当老师有多好了。”
这就是我爸,一个执拗到有点可爱的人。
很多时候,我想用很放松的状态和他聊天,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而有趣的东西。结果经常会被斥责得灰头土脸,甚至上纲上线地认为我的某些幼稚的想法会让自己难以在社会上立足,迟早会被社会边缘化,而我被社会边缘化是让他不可想像的事。但是社会总有边缘人,而且主流和边缘也一直是在变的嘛,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边缘的,但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也可以是主流的,很难去一概而论。但是要让我父亲——一个有着50多年生活经验——从来对主流价值推崇备至的人,去了解边缘人视角和社会建构的其他可能,似乎难度大了点。
所以我是无法赞同一些同龄人持有那种观点,认为父母皆是祸害。当我重新梳理我跟我爸的关系的时候,发现经历很有意思的变化。
我爸是一个被跌宕起伏的故事写满的男人。革命年代因为劳动公分不够被迫放弃学业(当时他的成绩很好),第一批下海又经历了破产风波,两次事故导致的骨折让他在病床上度过了七八年的岁月。但是命运的起伏和生活的重压都被他这个并不粗壮的肩膀硬扛了下来。
在那个改天换地的蛮荒年代,我爸自然需要用他自己独有的一套价值观去跟不公的命运抗衡。这种价值观导致他在孩子的教育上就是——打!小时候的我经常挨打,考试成绩不好要挨打,跟邻家小孩打架要挨打,偷东西要挨打,撒谎顶撞还是要挨打。这就是中国式的虎妈狼爸式教育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逻辑。
提到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因为小时候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我爸他身体也一再遭受重创,这也导致我们父子情感互动的缺失,而且那个时候他的棍棒教育也招致了我对他的疏离。但是在我的青春期之后,自己也懂得自省,能够设身处地为父母着想,所以有段时间他甚至成为我的倾诉对象。
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冲动,就是急切地想在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学习到自己缺少的东西——钢铁般的毅力、果敢的判断力和乐观的处世态度。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像他那样强大的男人。
但是到了大学以后,自己的知识体系慢慢建立起来,就渐渐对他那套略显保守的教育方式产生抗拒。他大家长式的家庭和人生,有点大男人主义作风,在我这个对“新世界”如饥似渴的人面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比如做家务这种事吧,他基本不参与,甚至会对我妈沉醉在社交网络这点兴趣也横加干涉。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在生意场上独当一面的他,回到家中就像个孩童,我们得事事都围着他转。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代人相处和沟通多多少少都会存在的问题,彼此都会带着偏见和傲慢,共同筑起沟通的壁垒。我觉得他在面对新鲜事物和不同观点上的顽固自大,他觉得我在待人接物和人情世故上生疏漠然。他们这代人对青年人的关注绕不开金钱和婚姻家庭,我们的又何尝不是被海量的物质欲望充盈,在被异化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中气喘吁吁,惴惴不安,然后在朋友圈的100000+文章中幻想——被媒体建构出来的诗和远方?
所以我跟我爸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还算良好。而且,现阶段我也觉得再去把我的价值观和父辈的价值观做一个优劣的区分是有失偏颇的。我只知道,在这种价值观差异的情况下我会重申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这个自由我爸已经给到我了,那就换一种思维和他相处吧。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知道彼此需要对方。随着他的年纪慢慢变大,他需要家庭的温暖,宗族的延续,刚好婚姻和孩子都是我和女友不排斥的,就一拍即合了。至于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不太清楚,我们两代人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呢。
▽ 婚姻是人们建立链接的一种方式
婚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现在和我女朋友是同居状态,其实有点准婚姻生活的意思,就差一证书来确认关系而已。我觉得当你遇到那个你爱的人,并且两个人相处过程中磨合得很好的时候,一切都不是问题,你会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未来也是值得期待的。
现在我们两人的生活被很多有趣的东西填充了,而我们从事的又是自己喜欢,能体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奇点计划”的艺术项目,她也跟我共同创立并参与。所以在这种拥有共同价值观又尊重彼此自由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看电影,一起做饭或者异国穷游,就不会觉得单一枯燥。
我有个50多岁的朋友,是个建筑师,同时也有很多自由职业。他的女朋友30多岁,是个职业艺术家。他们两个没有结婚,但是育有一子,那个孩子就像天使一般。但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状态无法雇佣全职保姆,所以为了照顾这个孩子,女方三年没有任何创作,牺牲了很多。我在他家小住的那段时间,发现孩子给他们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意义。所以,人生有得有失,只要你的人生道路选择是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建立在他人的意愿上,是没有高低之分。
我认识一些人,TA的生活需要更换很多的性伴侣,这是TA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就像有些人坚持婚前守贞一样。我也看到很多人对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满是惶恐或者嗤之以鼻,其实没有必要,人与人建立链接的方式成千上万,只要你的选择不侵害到他人的自由,你就选择自己觉得舒适和必要的链接方式就可以了,何必对一个只存在于人类文明数百年的“一夫一妻”制度耿耿于怀呢?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就觉得两个人完全地以自由意志去结合,思想和境界也比较一致,并且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鲜的事物,这难道不是一段让人感觉愉悦的伴侣关系吗?
感谢对此篇文章作出贡献的所有人
采访对象,协助采访人永佳、小灰,文章校对人淑君
▼
点 击 阅 读 往 期 文 章
人在广州 | 我不想做伟大的人
人在广州 | 强扭的瓜不甜,但解渴
人在广州 | 做任何事都一样:先活下去
人在广州 | 不做没有生命力的“干花”
人在广州 | 我的路只有一条:抵抗到底
人在广州 | 男友骂我傻X,我报以沉默和游戏
HumanStory · 倾听城市人心声
HumanStory亟需您的关注和分享
我会努力为你呈现更多城市心声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