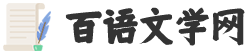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发表论文,不是科学家最重要的事。获奖更不是!”
“中国科学界可能对世界科学的独特贡献,不是有大批科学家在发表论文,得几个诺贝尔奖,而是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忘我精神和社会关怀注入科学界,及早解决世界上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几天前刚荣获格鲁伯(Gruber)神经科学奖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如是说。
格鲁伯国际研究奖每年颁发一次,旨在奖励在天文学、遗传学、神经科学三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对该领域发展有深远影响的科学家。
格鲁伯基金会表示,今年颁奖给蒲慕明,是为了表彰他在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评委会主席罗伯特·武尔茨(Robert Wurtz)赞赏“蒲慕明对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影响异常广泛”;2015年格鲁伯神经科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卡拉·沙茨(Carla Shatz)则表示,“通过创新和巧妙的实验,蒲慕明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大脑可塑性在神经细胞层面的认识——由于环境和经验影响,大脑神经细胞如何具有形成新的连接或改变已有连接强度的能力。”
现年67岁的蒲慕明,国际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出生于南京,成长于台湾,在美国工作了40多年,近20年又在上海工作。他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有篇报道中曾称他为“科学界的一位超级明星”,上海的同事们则说,“他比中国还中国”、“很久很久以前他便有一个中国梦”、“他在科研管理、科研布局等很多方面的贡献,不是一个国际学术大奖可以涵盖的”。
从2015年起,蒲慕明多了一个名衔: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任。关于备受关注的中国“脑计划”,很多人问过他到底何时才能启动实施。“‘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已被列入‘十三五’规划中100项重大科技工程的第4位。一体(脑认知原理)两翼(脑疾病诊治和脑机智能技术)的格局也已经确定。只是具体的启动时间和组织方法,尚未确定。”
蒲慕明告诉记者,人类早已进入21世纪,但在脑疾病领域却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药物。目前,脑疾病已成全世界的头号社会医疗负担,占比28%。如果到2050年还是如此的话,全球医疗系统将会崩溃。大家都知道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完全理解脑模拟脑是不可能的。但是,基于现有的知识,我们应该已能够对脑疾病问题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中国脑计划是以2030年为目标,如此长远的研究计划,若仓促启动,反而做不好。我相信,规划中国脑计划的实施该如何配合中国科研体制机制的改革,是该计划不贸然启动的原因之一。”
蒲先生认为,现行的中国科研体制机制,不适合研究重大的、长远的、非常花时间、不能马上出成果的科学问题。“真正的开创性科学成果常需要长期的专研才能获得。”他在神经所创建的系统创新的科研体系,包括率先引进国际化科研评估体系、人才招聘和流动机制,曾让他多次处于风口浪尖,而现在已成为国内科研机构的“路标”。
自2003年起,神经所已进行了七次国际同行学术评估,这里的新进研究组长和资深研究组长,每隔4年和6年都需接受一次评估,蒲慕明会根据评审结果,做出是否续聘、晋升、科研经费分配以及个人薪酬调整等决定。“我们就是要让科研人员有精力、时间、经费去攻克重大科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尽快出文章’。”攻克重大科学问题需要团队,但现有的评审体系都以个人独立完成的成果为主。为此,神经所又在计划尝试新的改革,未来,对于大课题团队中的一员,只要专家评审认为其工作是完成团队成果所必需的,考核时就可以按百分百计算,不再打折扣。
(我国改革开放后,蒲慕明马上投身到恢复和建设中国生物学研究的工作中,先后主持神经生理学、细胞膜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等系列培训班)
蒲慕明本科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博士后则是在美国普渡大学生命科学系完成的。交叉学科之重要,他太明白了。
如今,他还是“脑科学与智能技术融合研究”的倡导者,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的结合也将成为中国脑计划的招牌特色。今年起,,卓越中心目前已有20多个参与单位,他要求每人每年在交叉学科的研究机构蹲点2周以上,开课开讲座讨论问题。蒲先生自己已经去北京自动化所蹲了两次点,在那里开设了“人工智能的脑科学”讲座。“交叉学科蹲点和双导师带研究生,将成为中心年终评审的重要指标。”
神经所的基础研究成果,,耗能显著性降低。反之又如何?蒲慕明说,人工网络在过去也曾给他的神经科学研究带来了灵感。人工智能程序有输入端和输出端,最后一级输出端如有错,可以用计算机程序来调节输入端传递效率,这就是所谓“监督学习”时所用的“回递”程序。这么好的事,难道在神经系统中不会发生吗?蒲慕明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体外神经细胞实验中证实,神经细胞也可以做突触传递的反向调节。,后来又在动物在体实验中证实了这一点。“接下来,这些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将再次被放回人工神经网络,我认为,深度网络学习可以从中受益,大量节能减耗。”
蒲先生说,这项研究成果并不是此次获奖的原因,却是他迄今最满意的作品。“我的这篇论文,大概创了《自然》(Nature)杂志两个纪录,篇幅最长,引用最少; 因为脑科学的人不知其意义,人工智能的人不读神经科学的文章。但是我相信,最终这会被证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
(庆祝中国第一台自制单通道电记录仪成功,1982年8月于南开大学)
(单通道电生理记录研习班示范,1982年8月于南开大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内不少年轻科研人员患上了“诺贝尔奖疯狂症”,获得诺贝尔奖仿佛成了我国科学界最重要的目标。
蒲慕明说:“西方科学家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追求科学的初衷上有很大区别。西方科学家做科学是追求个人兴趣与个人成就,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得到诺贝尔奖就是科学家个人成就的最终表征;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是忘我精神,我们仰慕的大师是充满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现在国内很多优秀科学家是海归,在科研训练中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消失殆尽。“即便西方科技那么发达,还有那么多社会问题都没能解决,为什么?解决社会需求相关的问题,需要大批人的合作,也常不是诺贝尔奖重视的基础问题。我认为,未来我们要培养的科学家,要更富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要能关怀社会,解决社会的需求,这远比我国再得几个诺贝尔奖重要。
正是这样的蒲慕明,;80年代末起参与“认助中国乡村教育项目系列”工作,协助中国贫困地区提升教育质量和普及科技知识;自2005年起每年率领神经所师生开展科普支教活动,在四川雅安县和资阳县、安徽潜山县和无为县,3000多名中学生从中受益。在很多科教资源欠缺的地区,他捐款捐书,建立图书馆,举办教师培训,开展科普夏令营,改善实验室条件,资助困难学生。
然而,从1999年神经所建所直到2014年迁入新楼,蒲先生的办公室始终保持上世纪的简朴风格,从未要求重新装修,哪怕墙面已被雨水渗透。神经所成立至今,没有公车也没有司机。关于科研经费,蒲慕明总是希望课题组节约节约再节约,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是纳税人的钱,你们不能轻易浪费。”
受他的言传身教,蒲慕明的女儿蒲艾真少年时跟着父亲遍走贵州宁夏等祖国贫困山区,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投身于保护弱势群体的事业中,在美国成立了“全美家佣联盟”,促使纽约等各州议会先后通过家佣。蒲艾真2012年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大人物之一,,2014年被《财富》杂志选入世界上最重要的50位领袖人物——“她是其中最没钱的一个”,蒲慕明还长期用自己的收入资助女儿帮助弱势群体。“你们应该去采访她,她是我最敬佩的人。”
新民晚报记者 董纯蕾
图片来源:
(内含好多珍贵的老照片哦,蒲先生的粉丝们赶紧来找找,哪位是年轻时的“老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