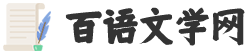一切研究,最初的起点,可能都在于对未知的渴求。大概从七、八岁起,我便对一切印有文字的纸片好奇;十岁开始,开始了较为系统的阅读,虽然彼时的读物,只是郑渊洁的《童话大王》。——也正是因为《童话大王》,打开了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窥探。一个人包办一本刊物的魄力,和汪洋恣肆而毫不节制的文字魔力,足以令一个小城少年感到惊异与神奇:原来文字可以这么写。及至长大,在鲁迅与钱锺书那里,又惊奇地发现了汉语写作另外两种臻于极致的风格:犀利、洞察、通达、幽默。逐年累积的阅读体验,不仅令一个少年神往大师的风采,也让少年转向了对文字和写作的痴迷,变成他对大师们拙劣而小心翼翼的摹仿。
文字不仅有巨大的魔力,还具有一种神力。在古人“敬惜字纸”的神圣规定里,字与字的连结不仅止于表达意思,还在于阐明意义:追问万物的起点,指向生命的最终路径。因而,无论是“文以载道”,抑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都意在表明,我们的文字书写,终究要体现为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应该是一种学术的自觉冲动,也应当包括学术的良知与审视,包括对时代、人生等终极“问题”的追问与思索,以求于回应当下乃至未来的“问题”。
从大学本科到博士阶段,三位导师令我终身受益。刘卓红教授作为我的博导,从入学开始,到论文框架的讨论、写作、修改,均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尤为让人感佩的是,刘老师的疏阔、爽朗与乐观,正与她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研究相当益彰。长江学者彭玉平教授是我在中大硕士阶段求学的导师,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至今让我铭记于心,并从中获得教益。与本科阶段杨立明老师的缘分,同样始于文字的往来。这是一位有着传统士人“古风”的知识分子,正直、睿智、理性而富有激情。我在她身边感受到的,不仅是严苛的训练,更是慈母般的关心与呵护。
感谢陈金龙教授严谨而温情的提点,感谢王宏维教授在我论文开题报告时所提出的中肯批评,使我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思路更为清晰、表述更为规范。也感谢参加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五位老师:华南理工大学刘社欣教授、中山大学王丽荣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王宏维教授、尹树广教授和霍新宾教授,他们既在充分肯定论文选题价值、内容结构和写作思路的同时,也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论文结构的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感谢博士学位论文隐名送审时几位专家的评阅意见,虽然自感论文远未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状态,但三位老师不约而同给了我“优”的评价,不仅使我受宠若惊,也更倍感肩上的重任: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答辩完成,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更长旅程的开始。
感谢好友张锐涛与我无数个“对谈”的瞬间,激发了我论文构思和写作中的无数个灵感。在论文写作和修改的每个阶段,他是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位听众。我以面对答辩委员会的心态,认真回答他所提出的每一个诘问和质疑;也以莫逆于心的知己角色,坦承自己的不足与缺陷。
求学华师的这些年,得以结识一群真诚而优秀的同学,是莫大的幸运与美妙的缘分。身为教授的刘梅老师,在已经取得卓越学术成绩之余仍然选择继续深造,对学术追求精益求精;朱斌、红军常常四两拨千斤,扎实的学术功底令人敬佩;占毅如兄长一般对我耳提面命、时时叮咛;思思、洁予、规娥、训梅,皆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无不让人感到一种温暖的力量。已经远在南昌大学工作、现已远赴英国继续深造的匡维博士,与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既在微信中谈学术研究,也聊生活近况,她对人类社会学的关注,和对教育学的深入研究,启发了我的论文写作思路。
小赖夫妇、晓丹、晓立、伟明、赖聪、侯杰、谭捷既是我的同事,也是好友。虽然彼此的性格、爱好迥异,但他们身上共同的一点在于:真实而真诚。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是温情的提点和关心;获取的,则是真诚的批评与匡扶。
感谢李聪、琼仪、晓琳、向阳、砾琳、顺平等小友。我见证并参与了他们的成长,这种共同成长的经历使我忘记了与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使我持续地保持了对生活的热情。
同样感谢我私友微信群里的诸位好友,这是一群天南地北而相识相知的“我们”。在群里,我们既探讨高深的学术问题,也分享彼此日常鸡零狗碎里的成长与体悟。“君子群而不党”,斯之谓也。
生命中奇妙的际遇,更是超越文本、文献的宝贵财富。读博这些年,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感慨而唏嘘的故事。2011年底的一场病,一度让我陷入极度的悲观和绝望。次年,我跨入30岁,而立之年。而一度,“立”也成为我一个艰难的梦想。——即便如此,我仍然毅然决然选择了“下乡”,参与政府旨在惠及更多贫苦农民的一项政策:扶贫。而下乡的那一天,近400公里的路程,一半以上是崎岖的山路,五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一路是靠着将座椅放平才得以勉力支撑抵达目的地。幸运的是,半年之后,一个乡村医生以他的妙手回春让我重新恢复了生龙活虎,让我得以继续行进在这片土地的大山大水。我一直坚信,这种生命中积极而充满希望的可能与转折,更像是一场能量的转移与反馈。我在2013年的新年献词中写道:“‘在路上’,就意味着发现和遇见更多的可能,也意味着,探寻生命既定‘结局’和‘归宿’的更多未知与奇妙”。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我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自驾滇川青藏、徒步雪山、穿行秘境,总行程逾20万公里。2015年盛夏,我负重徒步28小时,在滂沱大雨中夜宿于海拔4380米的营地,并于凌晨2时发起向蜀山之后——四姑娘山三峰的最后冲刺,并于8月18日凌晨7:04分雨夹雪中成功徒手登顶海拔5355米的三峰峰顶。从山脚起步到成功登顶,全程历时28个小时。而这,是我2015年川藏万里行的其中一个节点。另一个节点,在湘西吉首的丛莽深处,我驱车爬行湘川公路最为奇险的一段——矮寨公路,从湖南进入重庆。这一年,,而这一条奇崛的公路,最初的设计意图,正在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抗击日本侵略作提前的战略准备。
行走的力量,在于为自我生命的完整寻求更多的可能意义。十余年中,无数个远方、无数个身影,川藏线上磕长头的信徒、汶川地震的幸存者、甘孜色达天葬台主持葬仪的法师、蒙古草原上的没落王公后裔、,成为我生命中极为宝贵的财富,也成为我思考和写作的重要源泉。
正是在无数个曾经驻留的乡村、市镇与山野里,我看见了最为真实的中国。这,也促使我萌生了“回到”现场的冲动。2011年12月26日,,我启程奔赴梅州五华县周江镇黄华村,开始为期一年半的扶贫支教。在四百六十多个日子里,,不仅参与了由党的意志和行政命令所主导的新农村建设,也记录了这个乡村过去、现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故事。在完整将自己置身于山村田间地头、破败农房和残旧学校的2012年,我正好满30岁,而立之年。当我2013年3月1日正式结束扶贫工作,背起行囊回到广州之时,除了荣誉与经历,还多了一本厚厚的手稿:《黄华:,52万字的篇幅。
所有这些经历的背后,深藏着“家”的温暖。父母的爱,弥漫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我的命与运。我的父母是千万中国家庭中极为普通的一对,却是我心中最好的一对。父亲诞生于1949年,恰好与新中国同龄。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则死于后来被官方命名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之所以说“时期”而没有具体的一个时间点,是因为彼时父亲才10余岁,家庭的骤变和此后生活的艰辛,让他的“记忆”从此无法完整并复述。我的祖母,则是祖父在1949年之前新娶的另一房。在祖父猝然离世、留下两房两个老婆和七个子女之后,祖母承担了家道“中落”的全部重担。出嫁前的大家闺秀身份,转为地地道道的农妇;而父亲则在祖父离世近十年后,,成为一名军人,。祖母在临终前,:,没有,我们哪来今天的好日子?”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这种结构,恰好经历了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的三个历史阶段,亦即学者们所习称的“现代民族国家进程”。讲述这一段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可能再平常不过的家族史的目的,在于试图回答一个始终萦绕心头的疑问:为什么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苦难之后,?我在祖母去世半年之后考上了博士,于是,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成为我的学术研究的最初起点,也成为了我对祖母的一个特殊的纪念。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外甥女曦曦。这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孩,是她经常给我发微信,娇嗔地命令我:舅舅,不要那么辛苦哟,早点休息哦。她的笑,她的闹,成为我生命中温暖而强大的动力。在她两岁半的那一年腊月,我抱着她走向冬日的旷野,眼前的萧瑟与寂寥,引人无限遐思。曦曦在我怀里,突然用稚嫩的童声轻轻念出了一句:“空山不见人”,顿时,我泪满盈眶。这是一个幼小的生命对天地万物的自然感知与体悟,也是文化在生命之间传承、化育的奇迹。诗不在远方,端在眼前与刻下。
生命的另一种奇迹,则是相遇。所有一见钟情的缘分背后,其实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高度叠合。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无论成为朋友、抑或恋人,最令人向往的理想情谊莫过于旗鼓相当、莫逆于心。世人求良缘,往往以财、貌论,其实,真正的佳偶也正该是良友、益师,非止于花前月下、耳厮鬓摩,也当有红袖添香、素心砥砺。博士,美丽大方之余,聪慧而颖达,为我批阅全文,逐一订正字、句,几至于“锱铢必较”的地步。古人警告说“情深不寿”,可不也说了么,“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
此刻,我想静静。
毋庸讳言的是,这是整篇论文中写得最为随意、随性乃至放肆的一部分,因为这是全文唯一没有、也不需要引文的部分。真实的情感表达,无需引证诸他处或他人,而直接来自于内心。
世间一切相遇,都是命运所赐,于千万年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于千万人擦踵磨肩的迷乱的身影里,久别重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