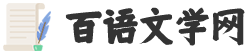写在前面的
论文终于写完啦
感慨很多
也有很多人要感谢
下一篇会写纪录片MFA的申请经验
终于来到了这趟旅程的终点。开始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要好好告别自己的学术生涯,然而在旅程结束的时候,我却已经决定要重新出发。正如文中所写:“经验,是你经历过然后因之改变的东西。”这篇论文亦是这样一场经验之旅。
与克拉考尔的第一次正式“相遇”,是在我对于学术意义最为怀疑的时候。一年多以前的那个下午,当我从图书馆借来《电影的本性》一书时,我已经决定了要离开象牙塔,开始了在新闻机构的实习,并计划去美国学习纪录片拍摄。出于对“电影理论”的补课需求,我匆匆翻开了这本“经典”“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的代表作,但出乎意料地被深深打动了。在一遍又一遍“恢复物质现实”、“不让主观超过客观的界限”的呼吁下,我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幼稚”的固执,而是一些更加微妙的,没有见形于笔端的关切。当时的我并非是由于热爱电影而想拍电影,却在这本书里找到了对于自己“不纯”动机的共鸣。
而在此之前,虽然我一直对齐美尔、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脉络很感兴趣,但对克拉考尔的印象却极为模糊:只知道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此刻不再这么认为了),甚至有时还把他和洛文塔尔弄混。读完《电影的本性》之后,我对克拉考尔产生了极大的好奇。这种好奇正是源于这个人物的模糊形象:既(不)是一个电影理论家,也(不)是一个社会理论家——正如那时和此时的我,既不是一个电影研究者,也不是一个致力于研究社会理论的学生,却偏偏总是游走在交叉地带。
研二下学期的这次相遇打乱了我原本的毕业论文计划。自研究生生涯起,我一直试图以“烹饪”为主题,做一份日常生活领域的经验研究,并与劳动分工问题勾连起来。但无论是在阅读文献还是在实践中,我都越来越觉得自己在“接地气”的同时越来越“不接地气”——日常生活批判实在是太轻易,太容易在“有趣”中化解一些无法化解的道德负担。在决定改做克拉考尔研究的毕业论文时,我内心仍然充满忐忑:基础不够、了解不多、方向不明,时间紧迫。如今,仍然非常感谢导师的鼓励,也庆幸自己的直觉和稚嫩的勇气。
开始走近克拉考尔的那段日子,恰好也是我申请纪录片硕士的关键时期。曾经无数次因此有强烈的负罪感——害怕因申请耽误论文写作,辜负老师的期许和自己曾经的学术梦想。在最为焦虑的时候,朋友曾经劝我分清“主次”,原本务实的提醒却在瞬间让我意识到自己最在意的不是申请结果,不是害怕没有好的去向,而是害怕对不起过往的三年硕士时光。
当然,耽误还是有的。如果真的一心向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或许我可以早一点学习德语,掌握真正的一手文献和二手研究,能够阅读书信集;可以对现象学、精神分析、齐美尔、本雅明、阿多诺等人有更加充分的了解;可以将自己对于艺术史的粗浅兴趣深耕下去,挖掘克拉考尔与瓦尔堡学派的关系;可以对意识形态问题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可以不在行文中犯一些低级错误……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缘分在于,如果真的那样一心一意,我或许就不会尝试迈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接触纪录片和那些让我“不舒服”的“物质现实”——或许根本不会与克拉考尔相遇,甚至相遇了也只是擦肩而已。
经验不是一次事件,而是一趟旅程,可能遭遇改变,也可能遭遇危险。个体拥有在不断改变中仍然保持某种同一性(identity)的能力。这是克拉考尔教会我的事。曾经一度责怪自己太“多变”而浮躁,从历史学,到社会学,再到离开社会学,中间还有无数次小的“转变”。当我觉得自己快支离破碎,但又无法抗拒这种离心力的关头,毫不夸张地说,是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重新给了我信念与定力。
如今仍然怀念最开始写作论文的那两个月,大概算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边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边输出的我,回到了最初被学术打动的状态。在专注中体验到了放下自我,回到一个时代,进入个人历史的感觉。在试图连缀这位思想家庞杂的兴趣时,我发现自己的破碎也得到了粘合——但不是在一个思想体系中,而是在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身上,在他的历史处境里。
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在研究风格和论文书写上的特点:不喜欢——甚至会回避过于抽象的讨论,喜欢具体和细节,喜欢镶嵌画一样的写作方式,喜欢本雅明用以形容克拉考尔的“拾荒者”形象,喜欢历史书写。这让我仿佛重新回到本科时作为历史系学生的原点,只是当时,我对于历史学与历史书写的想象过于狭隘了。
论文带给我最重要的东西,是在经历幻灭之后,意识到做一个研究者,仍然能够有支撑自己的力量。我发现,这种力量最终不是来自问题意识,时代关切,或者道德责任,而是来自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是作为读者和研究者的我面对克拉考尔的文字、生平和时代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一种打败死亡的东西,是人类的共同存在;这种历史感,也是当作为写作者的我在写下文字之后,所感受到的一种意义感:“将已经死亡的东西带回当下,为无名之物命名。”在这个基础之上,问题意识,时代关切,道德责任才会落实到一点一滴一砖一瓦之中,而不是在意义的深渊中膨胀成自大的惶恐。
在写作这篇论文时,我总是感到自己是在被牵引而行。原本计划的篇幅与内容在写作的过程中已经不具有约束力了,我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这样开心。直到发现这种“失控”,我才不得不反过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乃至更改未来的计划与安排,决定重新走上学术之路,哪怕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真正喜欢什么”或许永远是个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但重要的并不是心里到底如何想,而是要去做。
感谢我的导师李康老师。从我对学术萌生兴趣的大三,到写完硕士论文的今天,李老师一直是我学术之路上最重要的引领者,也是在我选择非学术道路时鼓励我探索学术边界的那个人。是他的引导、鼓励和包容,让我能够最终选择这个题目,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将它写出来。这篇论文是献给他的。
感谢戴锦华老师与我恳切长谈,她的鼓励与剖析令人有拨云见日之感。感谢胡泳老师,他的纪录片课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与他的交流也让人获益颇多。感谢李洋老师,他的电影美学课给了这篇论文非常多的启发。感谢密歇根大学的Johannes von Moltke教授认真回复我冒昧的邮件,他对于克拉考尔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详细介绍,也鼓舞了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后辈。
感谢曹金羽师兄。师兄的论文珠玉在前,是我学习的榜样。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耐心地给了我很多建议,分享了很多资料,和他的讨论总是非常有收获。感谢刘梦秋、李雪菲、余璐作为同行的伙伴,时常相互鼓舞。感谢她们愿意聆听我对于论文不甚高明的想法,仔细地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她们的陪伴是此刻和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我最珍惜的事。感谢在德国交换的范继敏帮助我在国图查阅1920年代的德国杂志,她的热情和耐心让人印象深刻。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港与北京电影学院的田风。在豆瓣上与他们结识,发现彼此都在研究克拉考尔之后,顿时觉得自己不再孤单。感谢那些热烈的讨论和分享,祝愿他们未来一切顺利。
感谢我的舍友周颖、贾晗琳、张楠,朋友刘偲、彭诗画。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因她们多了许多色彩与温暖。感谢她们在各种时刻给予我的安慰与支持,抱团取暖。祝愿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都将自己的信念坚持下去,努力幸福。
感谢正申请北大哲学系读博的高兴和香港大学的吴启慧,感谢她们在纪录片方面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感谢我们之间跨越学科的深入交流,激活了知识的魅力。无法想象没有她们的陪伴,我如何度过艰辛的申请季。感谢腾讯谷雨的李佳和记者夏偲婉,感谢佳姐对我的支持和推心置腹的理解,感谢小婉身上的勇气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和她们相处、学习、进步的日子是我最难忘的时光之一。
还要感谢现代科技和媒介的发展。感谢豆瓣网让友邻因分享知识而联结在一起,今天刚好是注册第9年,期待它成为中国的Academia。感谢Scrivener软件,是这个神器让我记性不好的大脑能够同时处理海量信息,将预期的5万字写到13万字,相信因为它学术之路会少一些痛苦。感谢Oxford Bibliographies为迅速了解各个领域的概况提供了最快捷的途径。感谢Northwestern的图书馆,让我能够借到许多在国内无法看到的英文书。感谢Library Genesis平台汇聚的大量文献,没有它就无法想象这篇论文的形成。
感谢我的家人。感谢父母对我无条件的支持、信任与爱。感谢爸爸教会我自尊与坚持,感谢妈妈教会我要热爱生活,做他们的女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感谢我的男朋友曾力玮,写完这篇论文也意味着我们即将结束三年异国,终能团聚。没有他我的人生或许是另一种样子,但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我也还是最喜欢有他的这一种。就这篇论文而言,感谢他一次次往返图书馆替我借还七八百页的书而毫无怨言;就我过去和未来的人生而言,感谢他的存在,照亮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