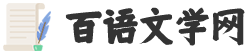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石头引】本周《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专栏,继续邀请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作者,来给大家分享博士论文创作背后的故事。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马强博士。
【个人简介】马强,,2011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其博士论文《“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获得2012年首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曾在《开放时代》、《世界民族》、《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俄罗斯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甲 结缘俄罗斯
人生际遇妙不可言,我与俄罗斯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刚上初中的时候,因父母工作调动,我来到了边境小城同江读书,这里与俄罗斯一江之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刚经历了苏联解体的俄罗斯与中国的边境贸易异常火热,。
当时为了满足边贸的需要,这里的中学外语课只开设俄语,转学以后,我只能从英语改成俄语。因为俄语,我们高考的外语成绩普遍比英语考生多十几分,有了这十几分,我跨过了北大的录取分数线。由于俄语在考学、就业中都受限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故意避开了俄语专业,进入了社会学系学习,以为从此和俄语、俄罗斯再无关联。但机缘巧合,大三的时候,正是因为我学过俄语,结识了高丙中教授。
高老师正在策划并实施着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计划,要把学生派往世界各地做调查。作为开拓者,他的博士生龚浩群已经前往泰国。高老师想把我纳入到这个计划之中,派到俄罗斯去。在西门外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里,高老师对我说,俄罗斯是中国最具对比性的国家,而中国人还并没有真正了解俄罗斯,这是海外民族志的使命,俄罗斯经验研究大有可为。
高老师的计划让我热血沸腾,从那时起,“到俄罗斯去做主体民族的田野调查,写一本关于俄罗斯的海外民族志”成为了以后十年的奋斗目标。博士毕业以后,因为在俄罗斯的经历和以俄罗斯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我想,我的学术生涯从此与俄罗斯再也无法分开了。
乙 准备下田野
自从有了赴俄的计划,我便开始着手准备赴俄罗斯做调查。当时,俄语已经扔了几年,几近荒废。为了训练俄语,我找俄罗斯留学生做语伴,在北语培训语言。后来发现,这些训练对出国调查来说远远不够,只有在国外的语言环境之中,语言的长进是最快的。
进入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修了很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课程。我发现,俄罗斯经验研究非常之少,在苏联时代,政府禁止西方人类学者进入,苏联解体后有分量有深度的民族志也是凤毛麟角;本国的研究多是民族学的路径,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对主体民族关注较少。
对中国人类学而言,俄罗斯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没有前人研究的积淀,让我失去了方向感和问题意识。去俄罗斯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能在俄罗斯社会中提炼出什么研究主题,只是懵懂地觉得苏联解体以后的社会变迁将会是一个研究维度。在开题报告会上,我清楚地记得,老师们认为我在俄罗斯研究方面“还是一张白纸”。我后来发现,在这张没有被勾画的“白纸”上,用在当地的亲身经历和第一手材料可以将俄罗斯社会更为真实、细腻地呈现。
2007年12月初,我通过“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来到莫斯科。十分感激这个项目,它能让我有了正式的身份(这在俄罗斯尤为重要),而且为了保证了调查时间,一再为我延期。还记得飞机到达的那天,莫斯科正下着雪,就这样,我踏着雪走进了俄罗斯田野。
丙 田野调查的不确定性
我曾经几次在“海外民族志讲习班”分享田野调查经验,我都讲的是田野调查的不确定性,我想这是最值得后来者借鉴的。
来俄之前,我自认为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到了俄罗斯以后才发现,这些准备远远不够。临行前,高老师和我有次长谈,他对田野工作有三个最基本的要求:学习和使用当地的语言;住到当地人的家庭;时间是一年以上。
我来到莫斯科以后,语言学习和时间都是有保障的,但就是无法住到俄罗斯家庭之中。在我的想象中,“田野”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小岛,是非洲大陆上的一个部落,而在莫斯科冷漠的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我不知道我的“田野”在哪里。在这里,如果你没有特别密切的私人关系,很难住到别人家中;到处都是保安、门卫、门禁的大楼,我不知道社区在哪里。
由于没有明确的调查主题,我总在要求找到“典型”的俄罗斯家庭,体验“最俄罗斯”的生活。而在多样性、多元化的现代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最俄罗斯”的生活连俄罗斯人自己都没有统一的认识。对“田野”幼稚的浪漫主义想象让我十分焦虑,这种焦虑在根本上就是调查主题和调查地点的双重不确定性导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预调查”在田野工作中是有着重要意义。对我个人而言,我的“预调查”是在不断试错中完成的。
丁 陷入田野
2009年,终于出现了转机,我来到俄南部的黑土区,住进了俄罗斯人家庭。如果说在莫斯科的经历是浮在田野之上,很难进入的话,最初来到黑土区的日子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田野中不能自拔。
年初,经一位中国朋友介绍,他的俄罗斯房东斯维塔阿姨接纳了我,她住在距莫斯科500公里的沃罗涅日市,。斯维塔是在城市中独居的退休工人,但她每天要到郊外的菜园(达恰)干活。初到沃罗涅日的时候,我每天都和斯维塔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帮着她翻地、种菜。后来,我在黑土区辗转于几个田野点之间,但闲暇时总要回到斯维塔这里,她城里的住所和乡下的菜园是我在沃罗涅日的家。
刚来的时候,冰雪还未消融,我们从山下农家拉来牛粪、鸡粪给地上肥。油油的黑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初春,刚刚烧掉去年的枯草,转眼便是新绿。洒下种子,小苗几天后便破土而出。五六月间,草莓已经红透,樱桃挂满枝头,之后,杏、马林果、树莓,还有一些不知名字的野果便能吃到嘴边。盛夏至初秋是收获的季节,菜园里的西红柿、黄瓜、胡萝卜、土豆、洋葱、圆白菜装满仓房。秋高气爽,树枝上的苹果泛着红晕;深秋转寒,霜打的葡萄正甜。第一场雪飘过,人们就很少去达恰了,期待着来年春暖花开。
这是俄罗斯市民诗意的栖居,但却不是我的田野。达恰区不是一个正常的社区,且被认为是一个用于休闲的私密空间,我很难进入。那一段时间,除了斯维塔,我几乎没有别的报道人。
2009年春夏之交,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斯维塔介绍我住进了达恰区附近的拉德诺耶村。房东薇拉是斯维塔多年好友,家里养着奶牛和各种家禽,出售自产的牛奶和鸡蛋,这些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颇受城里人的亲睐。薇拉和丈夫都在城里有工作,儿子刚刚考上大学,也不在家。所以,我住进薇拉家后,自然成了她家的帮手,喂牛、放牛、抬牛奶、卖牛奶、喂鸡、喂鹅……很多活计都要我帮忙打理。
薇拉是一个很好的报道人,随时回答我无穷无尽的问题,介绍周围的邻居和买牛奶的顾客和我认识,领着我去她娘家串门,带我去教堂参加礼拜。彼得洛维奇教我干农活,教我说只有男人之间才能讲的俚语,教我讲笑话,教我喝酒,还要教我射击、开车,他要把我变成一个地道的俄罗斯男人。
我很快融入了这个家庭,甚至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可以把各种事料理得井井有条。但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由开始的新奇、兴奋逐渐感到了一种束缚感。我进入这个家庭过深,我在从早到晚的各种农活之中不能脱身,更无法进入社区。薇拉和彼得洛维奇希望我能成为家里的“伙计”,而我想成为一个自由的田野调查者。我们认真谈过,但无法达成一致,最后,我选择了离开。
戊 意外的“多点民族志”
虽然寻找田野再一次失败,但是我并没有如在莫斯科那般懊丧。在黑土区城乡几个月的经历让我发现很多有趣的田野故事,让我对俄罗斯社会变迁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这些经历让我逐渐有了方向感和问题意识,一方面,,俄罗斯乡村生计方式、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另一方面,。
这段时间的经历不啻于做了一次预调查,这让我更加坚定地将黑土区乡村作为我的田野点。为此,我走访了沃罗涅日市可能做田野调查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沃罗涅日大学民俗学专业教师的推荐下,我又考察了黑土区的两个村庄。
最后,我选择了距离沃罗涅日市100公里的塞硕夫卡村。在房东夫妇的帮助下,我当地移民局办理了正式的居留身份。他们还在村里经营着баня(俄罗斯蒸汽浴室),我和村里的很多人都是在浴室里认识的。在这个村里我能自由地活动,能与村民更为深入地交流。村里的公共空间,如教堂、学校、村委会都对我开放。这些条件对于国内的田野调查来说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我得到这些却经历了如此艰难的过程。
我所经历的田野地点是具有多样性的,有大都市(莫斯科)、中等城市(沃罗涅日)、小城镇和黑土区乡村。即使是乡村,它们也是不同的:有的位于城郊,有的是城里人的休闲地,有的是传统的农业村落。在不同的地方,一些共同的东西却深深地吸引着我。每个地方,哪怕是最偏远的小村庄都和整个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都经历了社会变迁,并开始重建。也许在物质条件上有差别,但是它们在精神生活中是一体的:共同的信仰和传统,共享象征符号体系,共度节庆等等。
我在俄罗斯城乡(主要位于黑土区)的田野点所观察和体验到的共同之处,这是一个共同的俄罗斯,这也是后文被我称之为“俄罗斯心灵”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因田野调查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并不是有意为之的“多点民族志”却是有益的实践。
己 学做田野
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经常把田野调查称为“做田野”,这告诉我们,“田野”不是客观地在那里,而是做出来的,且做法因人而异。在这里我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希望对后来者有借鉴之用。
树立一个有益无害的形象。在一个社区突然出现外国人,且总在打听各种事,难免让当地人有紧张的情绪。记得刚到塞硕夫卡的时候,访谈过一个老奶奶,随手送给了她一个景泰蓝指甲刀作为礼物。我走之后,老奶奶拿出了指甲刀比划了半天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是项链坠,也不是摆件。她害怕起来,估计把我想象成里神秘的东方术士,怀疑我给她的这个怪异的东西有神秘的力量。为此,她一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给我的房东打电话让我把这个怪东西拿走。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我在当地人眼中是很怪异的,会给他们不安全感。我开始有意识地多出现在公共活动之中,让社区的精英,比如教堂的神父、村长、校长、前集体农庄主席向大家介绍我的身份和住在这里的目的,逐渐让人们打消对我的疑虑。经过几次露面以后,这里的人逐渐对我产生了信任感,再去见人、访谈就方便多了。
利用当地的成文资料。在现代社会,当地人会用很多方式记录他们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如形成于文字、档案、实物等。在俄罗斯,遍布于城乡的公共文化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地方志博物馆)为寻找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记得我送给档案馆管理员一包茶叶,她把我所在村庄集体农庄时期的档案全都搬了出来让我随便记录和拍摄;在地方志博物馆,义务讲解员生动地在“俄罗斯小屋”里为我讲述农民的生产生活;在图书馆的地方志阅览室,我可以查阅1920年代开始创刊的地方报纸。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我们所在社区的历史和现实极为重要。
使自己时刻保持新鲜感。“文化惊诧”经常被有田野经验的人津津乐道,我自己也深有体会,翻看田野笔记,很多有意思的发现都发生在“文化惊诧”之中。但人毕竟不是搜集资料的机器,田野之中,人难免有惰性,经历了开始的文化“惊诧”与兴奋,慢慢适应周围的一切以后,就会失去新奇感。而此时,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要提醒自己要时刻保持对田野的新鲜感。为了保持新鲜感,要勇于跳出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按照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调整自己,认识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事,你会发现,你的眼前又会出现一片新的世界。
庚 做一只酿蜜的工蜂
在俄罗斯,我听过一个智者总结的做学问的三种方式和境界:第一种是“老鼠”,它总是偷别人现成的成果据为己有;第二种是“松鼠”,它能采来各种果实拼凑成自己的成果;而第三种是“蜜蜂”,将花蜜采来酿成蜂蜜,是一种付出辛劳与智慧的创作。我觉得,田野调查者都是“蜜蜂”,花丛中采撷,蜂房里酿蜜。田野调查、撰写论文就是采蜜和酿蜜的过程,采蜜虽然辛苦,但如何将庞杂的材料,按照学术规范“酿成”一本民族志,这个过程也很艰辛。
田野归来,大概有近一年的时间我都沉浸在浩瀚的田野材料中,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笔。后来,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访谈材料、田野笔记、观察手记在有限的时间内是整理不完的,我要边写边整理。
我们海外民族志团队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从田野回来的人都要做报告,开始的时候,我的报告太注重细枝末节,要把所见所闻所想全部讲出来,大家听得云里雾里。大家建议我要找到一条线索把这些材料串联起来,最好使用一个当地的概念。这启发了我,我反复琢磨当地人是如何表述社会变迁的,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心灵”这个概念逐渐走入我的视线。
最初,我将“俄罗斯心灵”看成俄罗斯人身份认同的标准,后来发现,它不只是民族身份乃至公民身份,,更是指以“俄罗斯心灵”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人们把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变迁可以归纳为“俄罗斯心灵的回归”。这个概念的发现让我异常兴奋,围绕着这个概念来为论文搭建框架。但我太执着于弄清“俄罗斯心灵”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这又让我走进死胡同。我发现对于“俄罗斯心灵”的阐述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当论文再一次陷入困境时,师长和同门的建议与点拨再一次启发了我。我换了思路,“俄罗斯心灵”可能就是没有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表述,因为这是一个实践性概念。每个时代会对“俄罗斯心灵”有着不同的态度,而这恰好构成了对社会变迁的解释框架。在各个时代是如何“俄罗斯心灵”被生产与再生产,这成了表述与呈现俄罗斯社会的一个路径。有了这个框架,我的思路一下子就清晰起来,真的感觉豁然开朗。接下来,如何理论对话、谋篇布局、推敲字句,都是技术性问题了。
2011年6月,我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2012年,获得了余天休基金会的褒奖,这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今年,已经将改好的书稿交到出版社,作为“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中的一本,《“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出版。十年以来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与写作告一段落。去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我再一次赴俄进行田野调查,这次的主题是关于俄罗斯社会自组织。在我的学术生命中,我不会停下田野调查的脚步,不会停止对俄罗斯社会、俄罗斯文明的探寻,做一只辛劳的工蜂,奔波在中俄之间。
马强
于顿河畔罗斯托夫
2016年3月25日
【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往期文章目录
黎相宜:我去美国做田野
长按下图二维码,关注学术与社会(W-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