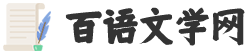(作者在从独乡到西藏察隅的调研路上 陈永群/摄)
也就是在《扎西》的作者次仁群宗完成硕士论文的那个答辩季,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也有一篇类似的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蒋易澄,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4。后文简称《母亲》),因为我在看这篇论文的过程中在微博上吐露了一些心声,那篇论文及作者(当然也包括我本人)最后成了媒体报道的对象。巧合的是,《母亲》一文也在今年被评为云南省的优秀硕士论文。两个应该是互不相识的作者,沿着相同的路数,做出了两篇内容完全不同,但风格十分相似的硕士论文,并且这两篇论文在两年之后均获得了“省优”。【至于“省优”是如何评的,本人从未参与过,一概不知】
直到开学前回到家里,坐在安静的书房里,我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较为认真地阅读了20余万字的《扎西》一文,加之最近一些年在康巴藏区做田野调查,对藏族以及藏文化有一点点粗浅的理解,我又突然萌生了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因此想对这篇硕士论文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我在此文开篇处就讲过,因为对于这篇(或类)论文(或这类问题)的讨论,已经涉及到学术评价标准的问题,虽然我也不能说我所讲的就是标准,并且,全国新闻传播学科五花八门的硕士论文,也很难用某种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但是在涉及《扎西》和《母亲》这样一种用人类学方法(或路径)来完成的论文,这和我自己的研究路径相同,可以谈一点看法。当然,即便如此,我在前面讲过,我所讲的也并非就一定是标准。或者说,这样的标准本身也是可以再做进一步讨论的。
(作者在从独乡到西藏察隅的调研路上写田野笔记 陈永群/摄)
2016年8月25日中午修订
(作者系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学术创新还是缺少规范?一篇“讲故事”的论文获奖引起的讨论(续)》
→→《“记叙文”也能获评优秀硕士论文?大咖告诉你为什么》
→→《获评省级优秀硕士论文,看看人家写点啥?》
......................................................
在这里,读懂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
在这里,探讨新闻业的未来
在这里,进行深入而严肃的思考
在这里,关心新闻人自己的命运!
......................................................
订阅《新闻记者》其实很方便——
您可以在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371,全年定价144元。
您也可以通过编辑部直接订阅,享受优惠价。订阅办法私信微信、微博小编,或电话021-62791234转324。
2016,《新闻记者》有你更精彩!